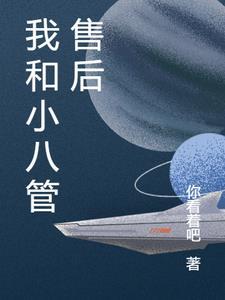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强宠骄婢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云舒听得连连皱眉,用写药方的纸盖住篮子道:“余夫人,那不是我相公,这些也不是坐胎用的药。”
余夫人笑着一搭她肩头,一脸促狭地看着她,“不是你相公?不是你相公你们住在一起啊?”
云舒一愣,眼神中流露出几分错愕。
余夫人急忙解释:“不是我到处打听你的私事啊!是有人注意到了那位公子,想着给他说媒呢,结果偏偏撞见了你们出双入对的情形,这一下子啊就在咱们这里传开了。”
云舒听后越发无奈,转而一想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便道:“没事,随便他们怎么说吧。”
她放好篮子,坐在了药师的位置上,却听外面传来一阵嘈杂,起初是几个百姓发生了口角,接着官兵前来清路,紧接着传来马车从石砖上匆匆碾过,又慢悠悠停下的声音。
对面包子铺的老板客人都伸着头往外看,余夫人也拉开了门,瞧着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云舒,你快过来!”
余夫人一边看一边朝云舒挥手,“你快看看那是不是你相……那是不是那谁!”
云舒有些疑惑,走到余夫人身旁,问:“谁啊?”
余夫人指着街口的方向,“那个,是不是那位公子?”
云舒眯着眼睛努力眺望,这才看清了薛恒的身影。
他头戴官帽,身穿墨蓝色的官袍,旁边站着两位年纪稍大些的官员,身后停着衙门的马车,大概刚刚离开衙门,又或者要赶回衙门里去。
无论他要去干什么,显然被人拦住了路,拦着他的人骑在一匹佩戴着赤金当户的白马之上,身材伟岸,因背对着云舒,使得云舒看不到他的样貌,但观其装束,似是一位皇子。
他身后同样停着一辆马车,珠顶华盖,奢美异常,坐在马车里的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便听那位皇子大笑几声,道:“还真是薛恒,薛世子啊,本王还以为自己认错了人呢。”
云舒愣住。
皇帝膝下子嗣单薄,皇后所生两子皆被废黜,这一位显然也不是纯贵妃的儿子,那便只能是朔王。
朔王常年征战在外,母亲是不大受宠的恪嫔,皇帝对他重用而不重视,从没考虑过将皇位传给他。
可他却回来了,在纯贵妃失宠,薛恒被贬的这个档口。
云舒隐隐觉得不妙,三两步走出回春堂,不顾官兵的阻拦往前挤了挤。
她由此看清了薛恒的神情,端的是从容不迫,云淡风轻,他抬头看着朔王,道:“朔王镇守辽安,何时到达的桐丘?”
朔王端坐在白马上,睨着薛恒道:“怎的薛大人连本王回京述职的事都不知道吗?也对,薛大人被父皇贬到了这穷山恶水之地,消息闭塞,探听不到京城发生的事实属正常。”
“劳烦朔王殿下亲自跑一趟将此消息告诉下官。”薛恒不徐不疾地道,“下次,差人送封信来即可。”
朔王双眼微眯。
他盯着薛恒,慢慢收起手中的马鞭,冷笑一声道:“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嘴巴还这么硬呢?”
薛恒无动于衷的看着朔王,眼神中甚至透着几丝怜悯,朔王满目讥讽的嘲笑,抬高声音对着马车里的人说道:“叔父,还不出来见见你的老朋友。”
车门打开,身披赤狐裘的瑞郡王走了出来,手里还撑着一根拐杖。
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面上戴着只金眼罩,似是瞎了左眼。看见薛恒,咬牙切齿地说了句:“薛世子,好久不见了!”
薛恒欠了欠身,含笑道:“瑞郡王有礼。”
瑞郡王觑着右眼,阴阳怪气地道:“我与朔王殿下途径桐丘,特来看望看望薛世子,薛世子在桐丘一切可好啊?”
“有劳瑞郡王记挂。”薛恒道,“下官一切都好。”
瑞郡王勃然大怒。
“一切都好?”
他猛地上前几步,贴在薛恒的身上,指着脸上的黄金眼罩,气道:“薛恒,你看看我的眼睛!你居然还有脸说出这样的狂言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