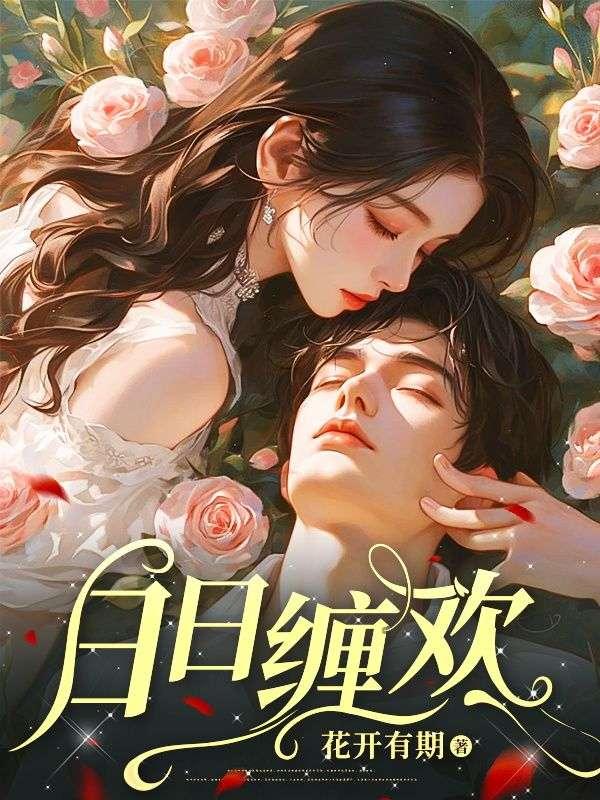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鬼捉鬼,我赚钱 > 7080(第3页)
7080(第3页)
张砚良反复吟诗,程不识端起酒杯却不入口,王舆与虞庆吃着从程家揣走的红枣也不吃酒。
傅元平皱眉,面露不解:“四位贤弟,今日为何与我如此生分?”
他的语气中,满是委屈。
程不识放下酒杯:“傅将军,程某有一事想问问你。”
“何事?”
“为何不送我们回家?”
傅元平的眉头,随着程不识的问话,拧成一道沟壑:“程贤弟何意?”
如死寂一般的沉默过后,王舆咽下最后一颗红枣:“傅将军,你明明已经认出埋在雪中的我们,为何将我们挖出来又丢掉?”
哐当——
酒壶落地,半壶葡萄酒倾倒,漏洒一地。恰似深红绸缎的葡萄酒,沿着青灰陶砖的纹路,一路晕开一幅锈色山河图。
傅元平弯腰拾起酒壶,惋惜道:“我一路带过来的好酒,四位贤弟却不领情。”
张砚良犹在吟诗,声量越来越高,吵得人委实心烦意乱。
忍无可忍之下,傅元平拍桌怒吼:“别念了!”
张砚良无知无畏,朗声念起另一首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2]
诗停之际,张砚良猛地起身,左手愤而指向傅元平:“傅元平,你丢弃同袍尸骨,不配为人!”
傅元平端坐主位,桀桀笑起来:“丢弃?若非本将有心,将你们三人拖到一块掩埋,你们只会和他们一样,被丢进深不见底的万人坑!”
那个坑足够大足够深,大到可以容纳一千余人的尸骨。
他们中,有些人因常埋雪下,尸身不见腐烂,又重又难搬。
兵卒们常与他诉苦:“这群死人,真是麻烦。”
挖出程不识三人的兵卒,是他的手下。
那人抢了程不识腰间的金坠子,来向他献宝:“将军,那边的厚雪下,挖出三具尸身,其中一个没有脑袋。”
他认出上面的“乌兰”二字,知是程不识之物。
想起往日的同袍之谊,他想了想让手下找出虞庆的脑袋,再将三人葬在一块。
他仁至义尽至此,纵使对不起所有人,唯独不欠他们三人!
傅元平的眼神,冷得像刀子:“死了,便好好去投胎,你们为什么又活了?!”
他们若活了。
那些到手的钱帛,便要拱手让出。
还有他的仕途甚至他的命,也会就此断送。
相比张砚良的气愤,程不识格外平静:“连你这种无耻小人都可以活,我们为何不能活?傅元平,你自小小旅帅擢升一方军使,全仗岩山血战之功勋。而今你坐享其成,竟这般苛待同袍。”
“你们本是死人,而今再死一次又何妨?”傅元平的眼神随语气逐渐凌厉骇人,“来人,动手!”
身后的门板,窸窸窣窣传来动静。
二郎腿轻翘,傅元平往后仰,闲适地靠在椅背等待。
不过须臾,四个持刀的男子出现在他的背后。
他看也未看,便径直下令:“杀了他们!”
语毕,一把刀却忽然横在他的脖颈间。
冷汗直冒,他顺着闪着寒光的刀往上看,却瞧见一个面生的男子:“你是谁?”
再一环顾,身后三人,亦是素未谋面:“你们是谁?他们呢?”
房门被打开,从暗处走出两个男人。
其中一人,身穿紫色圆领襕袍,腰间十三环蹀躞金玉带。
待看清来人的相貌,傅元平旋即瘫坐在椅子上,丝毫不敢妄动:“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