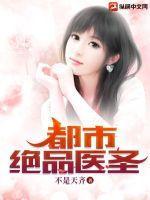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红楼:我是贾璉 > 第551章 迎来送往(第2页)
第551章 迎来送往(第2页)
如今的现状,中亚地区有西寧王的扩张,將沙俄支持的实力派清洗了一遍,远东还有一个李氏皇族的力量,饮马北海。
沙俄方面非常担心遭到来自东大与奥斯曼帝国的两面夹击,加上来自奥匈帝国的压力,战略上促使沙俄必须谨慎,否则三面受敌根本扛不住。
李清真是无力吐槽了,在內阁里头,他虽然是排第三,现在干起了迎来送往的活。
李清也意识到,因为摊丁入亩的事情,他在皇帝心目中实实在在减分了。所以,他才兢兢业业的不辞劳苦,做好分管礼部的本分工作。
其实对中亚地区的扩张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至少在马匹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作为与国內贸易的拳头產品,中亚高头大马的素质,明显是比蒙古马更有卖相。除了耐力差一点,其他方面几乎是完胜。这几年,大量的马匹从中亚运到京城,有钱人没一匹中亚產的好马,出门都没面子。
时间已经是四月底了,特意选择了走中亚路线的沙俄使团,这一路受到的震惊不可谓不小。
都是疆域广阔的大国,但存在很明显的差距。沙俄的大,是地广人稀的大,只有欧洲部分人口相对密集。东大的大,进入陕甘之后,明显能感觉的出来,沿途人口密度是要远远高於沙俄的。等到了长安,鲁缅采夫等人才对两国人口差距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么大一个城市,人口数十万,在东大居然在人口方面排不进前十。
通过了解,沙俄使团知道了一个事实,越往南方,人口越为稠密。北方以及西北的人口不多,完全是因为不適合种地。
说到人口眾数,接待官员也说不清楚,只能含混的表示,在两万万以上,毕竟上一次制定鱼鳞册,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两亿人口对於鲁缅采夫而言,也是很震撼的数字了。如果是个穷国弱国,倒也无所谓。但这是个大国,而且还超过沙俄的大国的强国富国,这个就很可怕了。东西方的思维底层逻辑有著本质性的区別,一个是世俗化社会,一个是宗教占思想主导的社会,思维逻辑能一样就是怪事了。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西方,首先是因为战爭成本无法承受而诞生的概念,其次是世俗权力与教权的角力,法国大革命期间又诞生了民-族主-义。
得知李清是內阁大臣,分管外交和教育,鲁缅采夫態度很好,表现的很谦逊和主动的热情。
但是李清也不是很给面子,实在是两国之间的交情不深,一度兵戎相见。加之此前接待的奥斯曼帝国使团,了解到沙俄一直在向外扩张,所以態度只能说维持了礼貌的客气。这种疏离非常的明显,接待了使团后,引入鸿臚寺的馆驛,李清就不管了,后续的事情后续再说吧。
这个態度让鲁缅采夫感到了深深的担忧,沙俄的强大是相对的,一路过来的见闻,让鲁缅采夫对东大感到深深的忌惮。尤其是进入京城周边后,水泥硬化的道路,让整个使团都產生了乡巴佬的自卑感。当然了,上一次有著同样感受的人,是奥斯曼帝国的使团。
英法作为欧洲的强国,主动与东大示好,缔结友好条约的原因,沙俄使团似乎找到了。
后续的谈判该如何进行,鲁缅采夫召集使团人员,紧急开会磋商。並且制定了一个原则,绝对不能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爭进行时,再与东大爆发战爭。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以往那种粗鲁的举动,希望使团的成员们都收敛一下,尤其是隨行的哈萨克骑兵。
也许是出於刻板印象,李清走之前交代了鸿臚寺,对於沙俄使团的成员,一定要看紧一点,绝对不允许他们闹事。出门要派人跟著,上街不许带武器,哪怕一把水果刀也不许带。
这个怎么说呢,李清回到內阁,向张庭恩交差时,忍不住吐槽:“俄人皆蛮夷也,看面相就知道了。”
真真是以貌取人了。
对此,张庭恩也没有责备李清的主观武断,反倒认可他的说法:“其人生於极北荒蛮之地,生性如此!前明英宗之时,不堪忍受瓦剌野蛮粗鲁,贪婪无度,才有了土木堡之战。虽说今非昔比,然则对蛮夷,不能以礼仪之邦来要求他们。只要不过分,忍一忍就是了。真要不能再忍,那也不必忍耐。”张庭恩压力不大的原因,前面有西寧王顶著呢,轮不到本土军队出战。
就算真的打起来,张庭恩也不怕,手里有一张叫贾璉的底牌,腰杆子就是硬气。
这真不是张庭恩自大,通过英法常驻公使,加之一些过去的记录,张庭恩看贾璉把欧洲强国的荷兰和西班牙都收拾的服服帖帖,害怕回沙俄?
对於沙俄使团的来到,张庭恩也没忘记派人给贾璉送信,徵求一下他的意见,毕竟这是大周公认的了解西方的第一人,杰出的外交家。
易卜拉欣抵达广州,贾璉给足了面子,亲率一眾官员迎接,並且设宴款待。
次日,易卜拉欣不顾旅途疲惫,迫不及待的求见贾璉。
俄土战爭打了五次了,奥斯曼帝国方面很清楚,下一次战爭时间已经不远了。
只能说,奥斯曼帝国在上一次主发起的战爭中失败后,一直在想著找回场子。
想要夺回刻赤海峡的控制权,那就必须打贏下一次战爭。
战爭嘛,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升级军备。
易卜拉欣这段时间也没少做功课,在会客室內坐下后,立刻先问问两个歌姬是否满意,喜欢的话他那多的是,下次再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