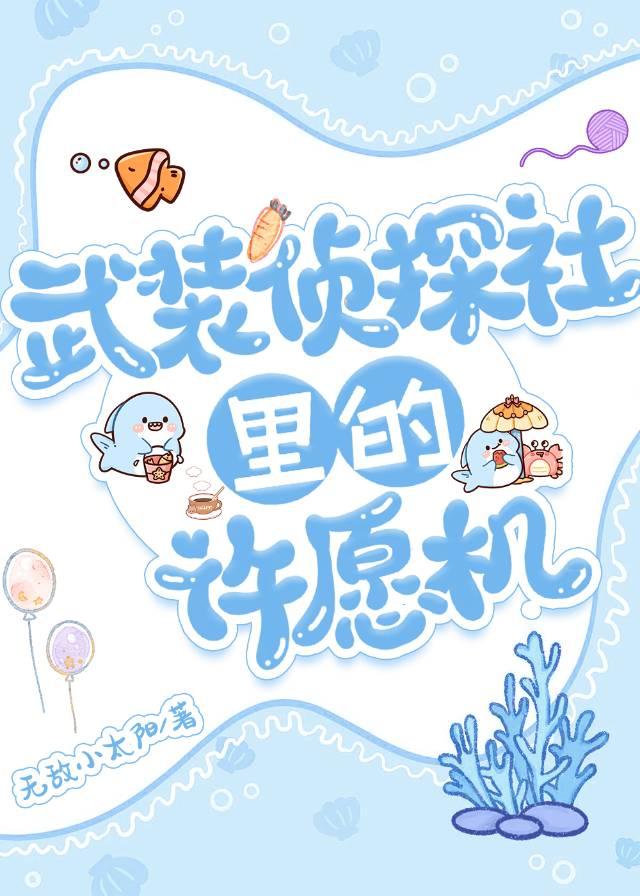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重生在90年代身披国旗[乒乓] > 2030(第41页)
2030(第41页)
混双的时候倒是没见到她使用,可能也不太熟练不敢乱用吧。
“本来想多练一会儿的,但第一次出去还是早点回来比较好,下午五点记得给我们开门。”朱淇坐在栏杆上,交代完这句后就跳了下去。
二人一溜烟跑到宋临州说的管理中心对面。
青年的声音夹着晚风,和滴滴答答的车链声交织在一起。
“你那个球是怎么拉出来的?为什么弹在桌子上能飞那么高啊?是你偷偷练的吗?”
“你知道‘马格努斯效应’吗?”
“那是什么?”宋临州没听说过。
“球在打出去的时候,因为有空气阻力的存在,旋转的球体两侧会出现空气流速差距。合适的角度、合适的旋转,拉出来的球弧线非常高,像半个圆圈,落到对方球台的时候因为上旋强会直接出界或者出高球。”朱淇补充一句。“我会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她’之前在日本队待过一段时间,日本队管这个叫‘弧圈球’,她学会了一点皮毛教给了我,但我也不是回回都能拉出来罢了。”
“原来如此。”宋临州声音微沉。
自行车匀速向前行驶着,朱淇坐在后车座上,深秋的冷风吹得脑袋有些凉。
骑车的青年可能脑袋后面长了个眼镜,腾出一只手不知道从哪儿拿出来一顶帽子,递给她。
朱淇说了声谢谢,扣在自己头上,她知道宋临州在担心什么。
他作为直板选手。
是未来最大的“弧圈球”受害者。
中华队90年代及其之前,因为大部分都是直板所以推崇近台快攻打法,利用直板的灵活性打落点变化得分。
“弧圈球”的出现就是为了用高强旋转来应对近台快攻打法,用旋转来克制摆速。
日本那边技术革新,在练“弧圈球”,到后期发展得非常成熟,甚至影响到了旁边的韩国和很多欧洲国家。
他们几乎能做到每一颗回球都得打出完美的弧圈球,这对直板大国、靠摆速得分的中华队来说就是毁灭性打击。
中华队也不是没有派人过去学习,但是一直不得要领,人家肯定也不会认真教。
朱淇前世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小教练,只能跟着俱乐部在国内的比赛里到处转转,也没有时间接触日本国手级别的“弧圈球”,只是在电视上看过而已。
但看和实践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世带她的体育老先生也用的直板,也不可能会“弧圈球”。
小姨父和江淮省队的教练们自然也不必说了。
他们连“弧圈球”是什么都不知道。
朱淇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练习中国版本的“弧圈球”,但是就是打不出日本队的高速度和强旋转。
和常红霞打出来的那个球虽然质量很高,但还是个七分熟制品。
而且还是在朱淇高度专注之下,爆发小宇宙拉出来的一个球。
目前只能希望通过大量练习,来摸索正确方法了。
公园里面出现两个年轻人。
本来在球桌旁边打球的大爷、叔叔、阿姨们觉得十分新奇,笑着打招呼。
“呦,这是哪儿来的俩小孩儿啊?”
“旁边儿国家队的吧,来我们这小公园儿玩来啦?”
“是的,耽误你们了,能腾给我们个桌子吗?”宋临州文质彬彬,谈吐儒雅,获得了大爷大妈们的喜爱。
有个穿着大马褂的老先生拎走了自己的包,让出一个桌子,乐乐呵呵道:“前来年也有几个国家队的小年轻,经常来我们这公园儿玩儿,后来他们还成了世运冠军呢。你们看着不大啊,多大啦?”
“刚18,来这儿练练球。”宋临州放下球包,把自己的球拍从包里抽出来的时候,旁边大爷们又哎哟一声。
“现在还有人练直板儿呢,不错不错。”
这搞得朱淇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横板拿出来了。
但大爷大妈们自动绕在旁边,做出了准备欣赏的模样:“来,你们拉几个球,看看你们啥水平儿。”
他们带来的球是白色大球,直板的旋转能力偏弱,朱淇尝试着拉了几个弧圈球但是没成功,全都打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