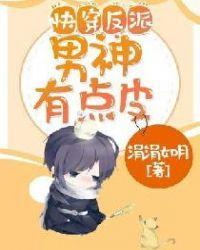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偏宠失控 > 她的反抗(第2页)
她的反抗(第2页)
雨声吞没了后半句话。
江羡站在原地,看着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成河。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屏幕亮起——
[谢临风]:比完赛了。伤口没事,别听媒体瞎说。
[谢临风]:[图片]
照片里是他裹着纱布的右手,比着幼稚的V字。背景是车队医疗室,角落露出半盒她上周寄去的低糖巧克力。
她的拇指悬在屏幕上方,突然想起去年冬天,谢临风在零下的赛道边等了她四小时。那天她临时加班,赶到时看见他裹着车队羽绒服,鼻子冻得通红,却笑着举起怀里的保温杯:“港式奶茶,你喜欢的。”
当时她问:“为什么不先去车里等?”
他答得理所当然:“怕你来了找不到我啊。”
雨越下越大。
江羡解锁手机,回复道:“明天我去机场接你。”
发完这条,她走向书房。推门前,她最后看了眼窗外——暴雨中的梧桐树仍在风中挺立,最顶端的新芽却已经被摧折,嫩绿的残骸挂在枝头,像面破碎的旗。
门开了。
江父正在批阅文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甚至没有抬起。“想通了?”
江羡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份信托文件。纸张在手中发出脆响。
“爸。”她第一次用这么平静的语气,“您知道吗?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二十岁那年听了您的话。”
江父终于抬头。
“如果当时我坚持去巴黎学艺术。。。。。。”江羡慢慢撕开文件,“现在应该过得比现在快乐得多。”
裂缝顺着纸张的纹理蔓延,像道终于决堤的坝。
空气凝固了几秒。
江羡忽然笑了。她放下酒杯,陶瓷杯底与大理石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咔哒”声。
“原来在您眼里,我的价值就是那点钱?”她声音很轻,却像刀锋划过,“好啊,您尽管冻结。”
江父瞳孔一缩:“你——”
“我二十八岁了,爸。”她打断他,每个字都咬得极重,“我不是您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她转身走向玄关,江父怒喝:“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就别回来!”
江羡的脚步顿了顿。她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对她发号施令——学金融、进投行、和谁交友、穿什么礼服。她总是顺从,因为那是“为了江家”。
但这一次,她不想再妥协了。
“爸,”她回头,眼眶发红,却笑得释然,“您知道吗?和谢临风在一起后,我才发现……原来被人毫无条件地偏爱,是这种感觉。”
说完,她推开门,踏入倾盆大雨中。
————
江羡站在机场到达大厅的玻璃幕墙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边缘。屏幕上还停留在谢临风最后一条消息:【落地了,等我。】
她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胸腔里那股翻涌的情绪。
昨晚的雨似乎还没从她骨子里蒸发干净,冷意丝丝缕缕地缠绕着她。父亲的震怒、媒体的追问、公司里那些意味深长的目光——她以为自己早已习惯刀枪不入,可当谢临风在电话里低声说“我改签了最早的航班”时,她的防线还是裂开了一道缝隙。
——原来她也会委屈。
广播里传来航班落地的提示音,江羡猛地抬头,目光死死盯住出口。人流开始涌动,她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声响。
然后她看到了他。
谢临风穿着黑色冲锋衣,戴着鸭舌帽,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他左肩挂着背包,右手拿着手机,眉头紧锁地扫视四周——直到视线与她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