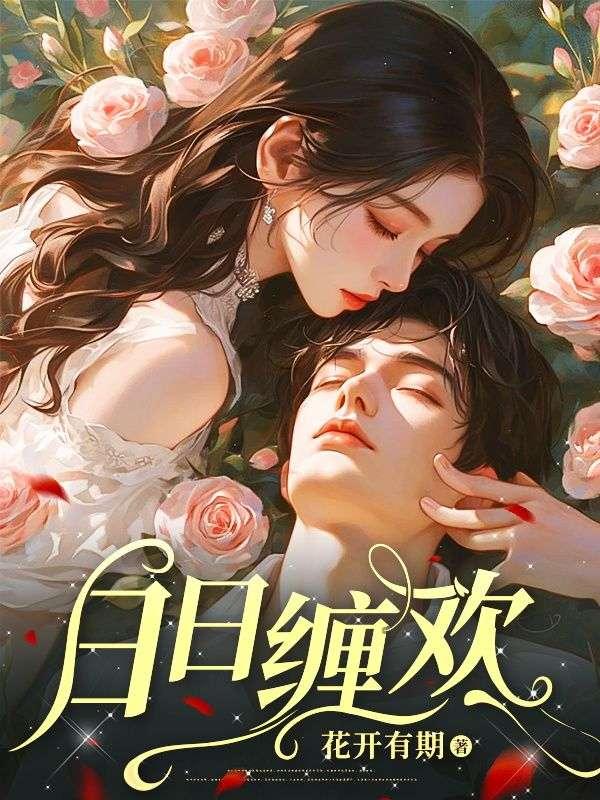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锁千秋 > 羊入虎口(第2页)
羊入虎口(第2页)
“反正不是鬼,小美人。”那人吊儿郎当地剔着牙,马灯在手里晃悠,橙黄的光忽明忽暗地扫过安终晏发白的脸,“两个小可怜,你们真该找个更靠谱的护卫。”
他往后伸手,揪出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可怜虫。千岁四肢被粗绳缠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了碎布,一脸尴尬地朝他俩眨眨眼。
“吓着了?”男人嘿嘿一笑,摆摆手,不知从哪里又窜出两个男人,“啧,去告诉当家的,又来了三个伕役,这回有个女的。”
安终晏几乎快把半张脸贴在纪初云背后,躲避着男人直勾勾的眼神,她害怕自己再看下去,会忍不住马上杀了他。
他们被粗鲁地赶到一辆老旧马车上。车板是拼接的,缝隙里嵌着干硬的泥块,边缘处磨得发亮,显然常年被人踩踏。千岁被其中一个男人像扔麻袋似的甩上车,“咚”一声撞在安终晏腿边。
“老实点!”车下传来呵斥声,随即“哐当”一声,车厢门被粗铁锁扣上,隔绝了外面的微光。
等车轮碾过碎石路,发出“咯噔咯噔”的颠簸声,安终晏才缓缓抬头。车厢里漆黑一片,只有从木板缝隙里漏进几缕微弱的光,勉强能看清纪初云正靠在车壁上,眉头紧蹙,千岁在自己脚边挪动着,被捂住的嘴不停“呜呜”响着。
“别乱叫。”安终晏用脚尖点了点千岁,“趁没人打搅,好好反思反思,怎么就被人悄无声息地抓了。”
纪初云:“羊入虎口,早该出手的。”
安终晏突然语调欢快起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都来了,总得看个明白。”
话音刚落,马车忽然急刹,三人都往前扑了扑。千岁撞在车壁上,再次发出一声“咚”的闷响,随即外面传来粗嘎的笑声:“到地方了,把这批货卸下来!”
车锁“咔嗒”被拧开,火把的光刺得他们眼睛生疼。安终晏看见两个举着火把的男人站在车下,脸上沾着黑灰,眼神像打量牲口似的扫过来。“动作快点!”其中一人用脚踹了踹车厢板,“当家的等着清点人数呢,耽误了时辰,小心扒了你们的皮!”
安终晏跟在纪初云身后下了马车,千岁被另一人割断身上绳索,扯出嘴里碎布,随即推搡下去。
安终晏打量周围环境。连绵的窝棚,是用破布和茅草搭成的,边角处结着层薄霜,在火光下泛着冷白的光。窝棚间的空地上,不少手持鞭子的壮汉围坐于火堆旁,此刻都在直勾勾地盯着他们看。
“搜身。”
“搜什么身。”将他们抓来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这两个细皮嫩肉的还能带什么武器不成?”
“哪另一个呢?”
“搜过了。”他将千岁的剑扔过去,“放在老地方就成。对了,当家的怎么说?”
“没回来呢,就按当家的嘱咐过的,先将他们关在竹楼里。”
男人可惜地咂咂嘴,眼神再次将安终晏从头到脚溜了一遍,像屠夫打量待宰的羔羊。安终晏地低下头,装作害怕的样子。
“那就去竹楼吧。”男人说。
所谓竹楼,是指一个被用围栏圈住的小村落。围栏是用碗口粗的毛竹拼接而成,十几间茅草屋东倒西歪地杵着,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露出黑黢黢的椽子,墙缝里塞着朝天翘起的干草。一群身穿粗布短打的人靠在一起,见他们被押进来,都停下手里的活,用麻木空洞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安终晏看见一老妪怀里抱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孩子的脸贴在她枯槁的手上,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半点声音。老妪的眼神同样空洞,见他们进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死气沉沉,毫无活力,是安终晏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等负责押送他们的人走了。一道坚毅的女声骤然响起,“这里很久没有外人来了,不管怎样,欢迎光临。”
一个壮实的女人从人群中站起。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肌肉线条在火把余光里绷得紧紧的,像是块被反复捶打的精铁。女人的眼睛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太亮了,像藏着两簇火,扫过来时带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她往那一站就能叫人看出她是这里的主心骨。
安终晏凑近女人身边。她见过这张脸,不过是更年轻的版本。
“您知道巧箐吗?”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