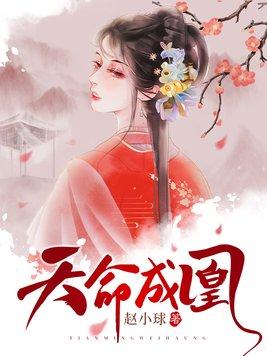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天赐良缘【GB】 > 第19章 魁油(第1页)
第19章 魁油(第1页)
万寿节刚过六日,圣京风云突变。
天宪司雷厉风行,一举擒获了包括前兵器所正监孙正革在内总共六位五品以上的涉事京官。
听审那日,天宪司公堂之内,皇帝大怒,抓起案前的令签,狠狠掷下。伴随着这一掷,六人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圣京这一番处置传到北地,当地官员一时间人人自危。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第七日的宫宴就此熄火时,宫内向在京公主、亲王和诸位朝臣下了帖子,邀请大家共度佳会。
宫道两旁,等待着进宫赴宴的队伍排起了长队。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和车轮碾压地面的辘辘声,响如雷霆,震如战鼓,直入宫门不下。
周遭众人闻此声,刹那间噤若寒蝉,纷纷惶恐避让,不敢有半分迟缓。
跟随大人入宫的孩童,好奇地想要张望,却被大人急忙捂住眼睛,拉至身后,低声呵斥:“那是大长公主的座驾,不得无礼。”
踏入宫门后,应灼到殿内落座。
贺遥默不作声,亦步亦趋跟在卫星朗身后。
待卫星朗入座,一众大臣便纷纷围拢过来,有人拱手道贺,有人旁敲侧击打听消息。
大家心里门清,这位天宪司监,而今也不过二十岁的年纪,天潢贵胄正当红,此前三年不在京内,这时见了总得烧烧灶。
薄暮时分,风云突变,刹那间电闪雷鸣。一记震耳欲聋的响雷乍响,惊得众人皆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太极殿外。
许多宫人神色匆匆,皆朝着御花园的方向疾步而去。
大雨如注,倾盆而泻。
贺遥满心疑惑,难不成外头有甚要紧之物?
卫星朗正在同邻座翰林学士交谈,贺遥悄悄凑近卫星朗,压低嗓音问道:“将军,他们这是做什么去?”
卫星朗亦微微倾身向前,声若蚊鸣,比贺遥所言更轻几分:“他们……”贺遥赶忙侧耳倾听,却仅仅听得一句:“夫人不是让我谨言慎行吗?此等宫闱之事,不得妄言。”
贺遥顿时语塞,无奈地与卫星朗拉开间距,神色幽怨,悻悻道:“将军所言极是。”
邻桌那翰林学士仍微微侧身,目光殷切,只待卫星朗回首,可接续方才被中断的话题。
岂料卫星朗的夫人不知为何闹了情绪,卫星朗赶忙倾身向前,凑上去说着小话。
翰林学士见状,原本伸长欲语的脖颈瞬间僵住,神色略显尴尬,只得缓缓坐回原处。
卫星朗轻拽着贺遥的臂膀,低低浅笑,温言软语地哄道:“罢了,莫要气闷,我不再逗你了。”
贺遥仿若已然适应了卫星朗这般孩子气的行径,转瞬之间,神色便恢复了往昔的平和,眼眸中闪烁着好奇的光亮,不自觉地凑近到卫星朗的跟前。
卫星朗瞧着他那不住闪烁的双眸,刹那间竟觉喉咙干涩,赶忙定了定心神,缓缓开口:“御花园的列阵台上有一稀世珍宝——杨氏长箭。杨氏长箭乃是一套弓箭,是礼王王妃母家杨氏的祖传宝物。弓长三尺,箭长二尺八,十石之力才能拉开。一旦开弓,开天辟地。除了杨氏族人,鲜少有人能驾驭,唯有太祖是个例外。”
言至此处,卫星朗想起之前母亲的猜测,神情渐渐凝重起来,“大宣开国时,杨氏一族追随太祖南征北战,几乎举族覆灭,唯有北地一脉幸存。杨氏长箭制作工艺极为繁复,且技法隐秘,如今早已失传,世上再无人能复刻。当年留存的杨氏长箭仅有两套,一套陈列在皇宫御花园列阵台,另一套由杨氏族人世代珍藏。宫里这套,一直由兵器所和杨氏族人共同维护保养。”
贺遥听入了迷,宣太祖开国的话本他也看过,眼中的好奇之色愈发浓郁,追问道:“当真有开天辟地之势?”
卫星朗点头:“那箭头足有一寸半粗细,箭尾之处则是采用极为罕见血灵鹄羽的特制而成。传闻太祖驰骋疆场,一箭射出,力穿五人。”
听到“血灵鹄”三字,贺遥眸光微动,似有灵光乍现。他下意识摩挲着肋骨,追问:“如此珍贵的宝物,怎会露天置于御花园,任凭风吹日晒?”
卫星朗解释道:“长箭常年置于皇帝寝宫,是自太祖时期便定下的规矩,意在让后世子孙铭记先辈创业的艰辛。而万寿节之时,则会把此箭挪去列阵台,见天日,知天威。定是司天台测算这几日无风无雪无雨,才将长箭挪了过去。可是此刻要将长箭再挪回来却不简单,想必列阵台那边此刻正手忙脚乱地搭建雨棚。”
卫星朗看着来回的宫人,微微眯起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