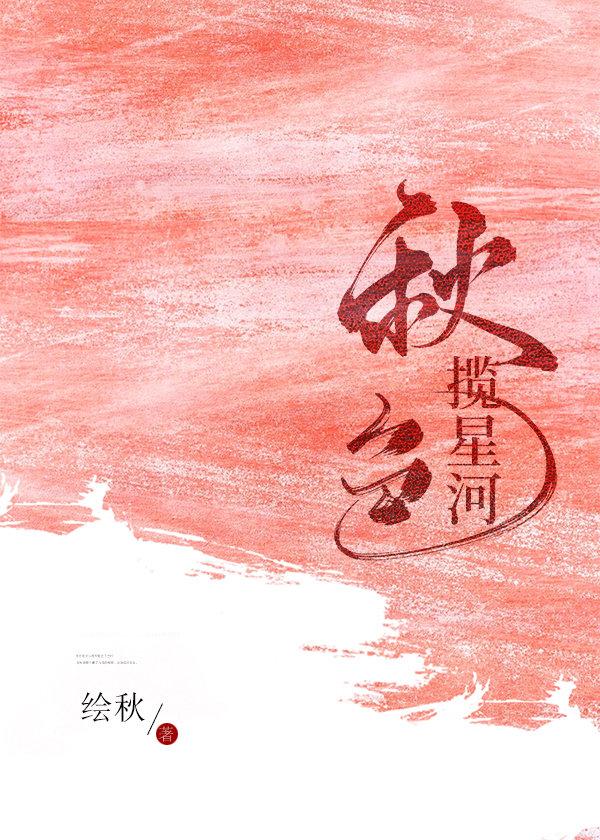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琼珠碎又圆 > 诛心(第1页)
诛心(第1页)
次日清晨,赵昱与韩溯赶赴江仙阁,昔日浮华旖旎之地,一夜之间变得死气沉沉。身着红袍官服的京兆尹亲自带二人去了瑶姿的房间,一路讲述了仵作验尸的结果,与赵昱判断无差,凶器是细管状利器。瑶姿的房间自案发就被封锁,物犹在,人已逝。韩溯径直走向梳妆台,打开菱花镜旁的描金妆奁,一层层检查,没有发现那根银簪。赵昱让把管事的叫来。
被拘了一夜的老鸨春娘蓬头垢面、十分憔悴,一进门便半跪半坐在地嚎啕大哭:“我可怜的瑶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好端端地就没了啊……”
韩溯毫不理会,冷冷问道:“瑶姿出事前可有什么异常?”
春娘立刻止住干嚎,抬眼看到韩溯,立即喜上眉梢,“唉哟,这是……韩公子吧,敢问公子在哪个衙门高就哇?”
京兆尹王敬之呵斥道:“问你话你就答,莫要攀扯!”
春娘吓了一噤,才老实回答:“没什么异常,自陈老爷下了聘后,瑶姿就不接客了,除了出门送请帖,就是筹备嫁妆,整个人喜气洋洋的,谁能料到会出这种事啊,唉哟我的心肝儿哦……”又号丧起来,毕竟瑶姿一死,那到手的聘礼就要飞了,实在肉疼得紧。早知会发生这种事,就该早几日将她嫁出去了事,白白连累老娘做生意。
“昨日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吗?”
“昨儿宾客盈门,我春娘是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姑娘们梳洗打扮、后厨采买供应、这楼里上上下下、桩桩件件哪个不要我操心的……”春娘越说越理直气壮,俨然忘了自己是被问讯之人,直到望见面前三人神色冷峻,尤其当中那人,器宇轩昂,好似打了郑大公子的那位,虽不着官服,威势盛过京兆尹大人,春娘阅人无数,知道这人了不得,再不敢造次,喉咙里咕隆了一声,低声补了一句:“实在没留意有什么可疑的人。”
韩溯了然,在春娘这等唯利是图之人眼里,瑶姿是已高价成交的商品,自不会再费心思在她身上,便问道:“瑶姿平素有要好的姐妹吗?”
“那就是芳姿了,您也是见过的。芳姿来得晚些,一直是瑶姿带她。”春娘的媚笑里带有几分暧昧的意味,可韩溯这个看起来脸皮薄的小白脸竟毫不变色。
芳姿被带了进来,眼睛已经哭肿了,柔柔弱弱的似带雨的蔷薇,韩溯换了较温和的语气问道:“芳姿姑娘,你可知瑶姿平日里与谁有过节?会不会有人眼红她脱籍从良、觅得富贵?”
芳姿连连摇头,声音哽咽,“瑶姿姐姐最是温柔不过的人,从不与人结怨的。我初来时不懂事,都亏了瑶姿姐姐替我转圜……我想不出有什么人这么恨她,姐姐死得太惨了,大人一定要为姐姐做主啊……”泪如断线,泣不成声。
“你素日同她在一起,你来看看,她的东西可曾有缺失?”
芳姿拭了泪,环视房间,打开箱笼、妆奁一一检视,回道:“东西都在,瑶姿姐姐昨夜献舞时除了一支从不离身的银簪子,什么都没有戴,我还说太素了,她说干干净净的才好。”
韩溯眉头蹙了一下,接着问道:“瑶姿出事前可有什么异常?”
芳姿思索良久,“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异常。那日,瑶姿姐姐看到妈妈送过来给她做嫁衣的绸布,就跑去问妈妈这布是哪来的,回来后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春娘见众人视线又落到自己身上,瞪了芳姿一眼,“别听小蹄子瞎说!瑶姿既然叫我一声妈妈,聘礼当然是我来管的,我也是好心捡了卷上好的绸布给她做嫁衣,怎么还落下不是了?那天瑶姿来也只是问问布是哪儿来的,她家官人开着十几间铺子,还能跟我计较这些?”
韩溯神色一凛,隐隐有种道不明的不详的感觉,他沉声问道:“聘礼在哪?”
春娘担心到手的聘礼不保却又无可奈何,极不情愿地说:“在、在我房里。”
春娘房里还残留着浓浓的脂粉香,令人头脑晕胀。艳红洒金的床帐边摞起几个大大小小的箱子。掀盖一看,里头尽是金灿灿成套的首饰头面,以及各色华彩的绫罗绸缎。韩溯下意识地捡起一支簪,转到背面,鳞纹印记赫然在目!他又翻开布匹绸缎,每卷都有个小小的却清晰的鳞纹印记!
韩溯感觉胸前气血翻腾,而脊背却发凉,他犹不死心,指着这些被翻得凌乱的箱子再次确认:“这是瑶姿的聘礼?”
“是呢,陈老爷一眼就瞧中了瑶姿,且不是纳妾,是明媒正娶做填房呢,看看这些聘礼,不知有多少姐妹羡慕……”春娘终于发现韩溯的脸色愈来愈难看,声音渐渐卡在喉间。
韩溯阖上眼睛,想起昨夜瑶姿的绝世之舞,她勘破龌龊真相的那一刻是否就存了这样自毁的念头?赵昱轻轻拍了拍他的肩,他睁开眼,看见对方的眼里流露出悲悯之色。韩溯轻轻地说:“她是自杀的。”
赵昱点点头,转身让人下水打捞银簪。银簪很快被捞起,经水的涤荡,没有一丝血迹,触手却是彻骨的寒凉。
赵昱对王敬之道:“敬之兄,这个案子可以结了,死者是自杀,这枚银簪就是凶器,但个中内情牵涉颇广,卷宗上还需敬之兄费心。”
王敬之脸上闪过一抹讶色,稍作思索,道:“这老鸨贪得无厌,致使楼里的姑娘轻生,罚钱三千贯,令其停业整改三月,如何?”
“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