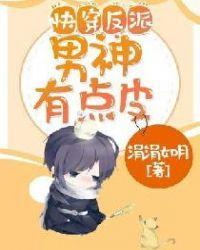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转生成甚尔女儿的我如何存活 > 东京长牙(第2页)
东京长牙(第2页)
我白了他一眼,继续耐心地尝试。但惠对米糊的兴趣显然还没有对勺子大,吃进去的全数吐了出来,剩下的则贡献给了围兜、餐椅和我的衣服。
“你小时候可没这么难搞。”甚尔说。
我顿了一下,然后擦掉惠下巴上残留的米糊。
在我的上一世,吃饭都要讲究礼仪规矩,挑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饭桌上也绝对不许说话。我至今记得被迫咽下讨厌食物的感觉,以及那个女人满意的微笑。
我曾一度厌恶吞咽食物的感觉,每次饭后都会偷偷去洗手间催吐掉,以至于身体状况奇差,哪怕后来在高中时逃出了那个家,这个状况也没有丝毫缓解。
直到我来到这里,遇见了雪穗。
甚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走过来,先是拍了拍我的脑袋,然后又粗鲁地揉了揉惠的头发:“挑食长不高,你看你姐现在就矮。”
我瞪大眼睛反驳道:“喂喂!哪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而且我比同龄女孩子已经高出一截了好吗!”
惠则抓住他的手指就要往嘴里塞——新长的牙硌在甚尔手上的老茧上,两人同时愣住了。一个大概是惊讶于手指的触感,一个震惊于牙齿的存在。
(四)
某天半夜我醒来,发现小床里的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我心慌地跑到客厅,发现厨房亮着灯。
我疑惑之余推门进去,结果看见甚尔站在灶台前正煮着什么,惠坐在料理台上,正津津有味地啃一块磨牙饼干。这个画面冲击性有点强,以至于我愣在原地好几秒。
“……你们在干什么?”好半天后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甚尔头也不回:“炖南瓜,夏油说的,他儿子以前就吃这个。”
我踮脚去看,锅里确实是南瓜,已经被炖得软烂。甚尔用勺子将橙黄色的瓜肉压成泥,惠伸长脖子去够,被他用一根手指抵住脑门推开。
“放凉。”他说。
我靠在一边,看着甚尔试温度,蒸汽模糊了他的轮廓,让这个场景显得格外不真实。惠咿咿呀呀地伸手,这次甚尔没再阻止,而是舀了一小勺南瓜泥送到他嘴边。
惠乖巧地张开嘴,甚尔的嘴角微不可察地上扬,又很快恢复平常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之前送走孔时雨的时候那个男人说,他从不知道哪里得知的小道消息,甚尔小时候经常饿肚子。禅院家不会给“废物”准备像样的饭菜,他大概是从垃圾堆里学会分辨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的。而现在,他却在深夜为自己的儿子煮南瓜泥。
我捏了捏鼻尖,感觉有点酸麻。
(五)
最后还是南瓜泥在一众辅食中胜出。
第二天早餐时,我特意准备了新的南瓜泥,惠表示很喜欢。
甚尔坐在对面跟夏油真吾打电话,手机里传来某位漫画家得意的大笑:“我就说吧,杰就是吃着我做的南瓜泥长大的!”以及夏油杰无奈地劝阻声。
惠朝我们咯咯笑,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餐桌上,照亮了飘浮的尘埃,甚尔伸手戳了戳惠鼓起的脸颊,换来一声不满的抗议。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些东西。甚尔可能永远学不会如何做一个普通的父亲,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照顾我们——当年没人教他怎么当个孩子,他却知道怎么不让我们重蹈自己的覆辙。
这个并不温柔的男人,正在用他全部的温柔对待我们。
(六)
长牙期的惠变得格外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