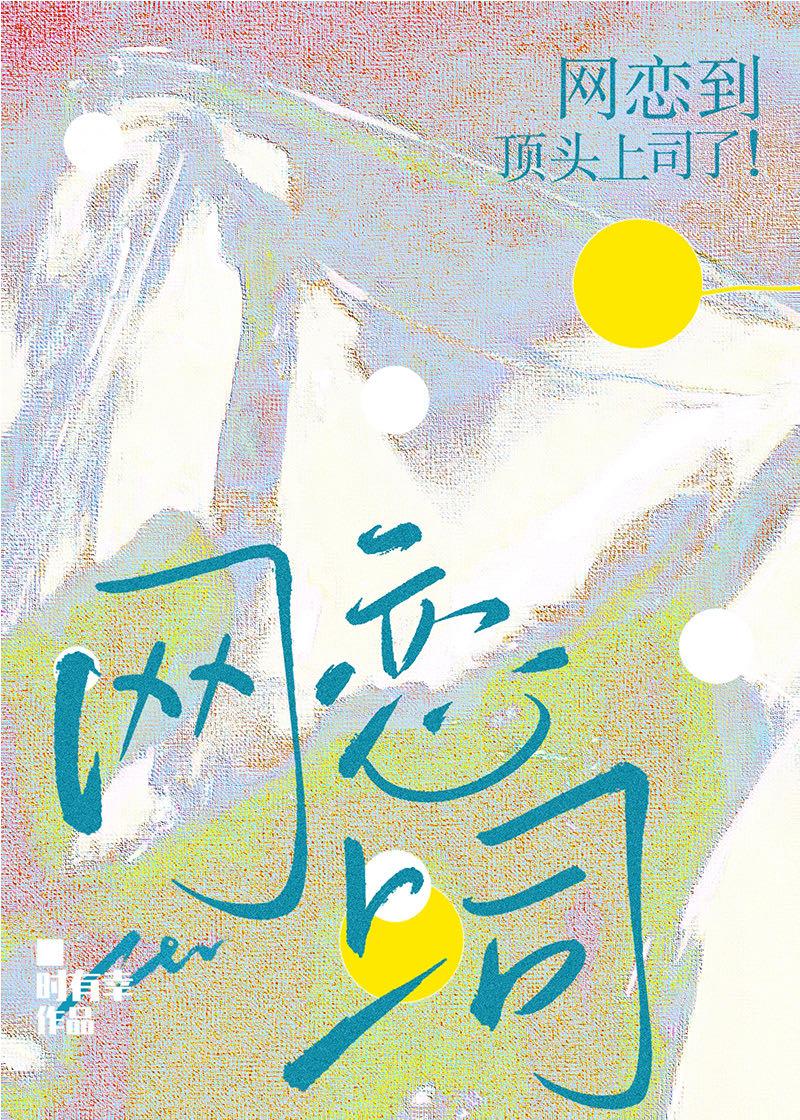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临安杏花饭馆(美食) > 5060(第2页)
5060(第2页)
谢临川听罢,心里就是一个咯噔。
他何等聪明,父子二人间的几句话,他已经弄清楚了个大概。
眼见得薛廉两道目光利剑似的射向自己,他就摸了摸鼻子,斟酌道:“此事是我的不是。推门的时候,手劲儿大了些。”
他两个一唱一和,真有这么回事儿似的。而一旁的薛廉,简直要无能狂怒了!
碍着谢临川这个外人在,不好发作,他就一扭头,气冲冲地往内院里走。
薛齐跟在其身后,亦步亦趋:“父亲大人,您仔细些,免得跌了跤。”
“若是跌了,兄长们又赴任在外,免不得还是不孝子我,和不孝媳雅里来照顾您。”
薛廉一听,气得胡子都歪了,脚步却真的慢了下来。
薛齐与萧雅里两个,趁机一左一右扶着薛廉的胳膊,状若虔敬,实则促狭,把人夹着往前走。
谢临川抱着手臂在后头看,简直乐不可支。
能把大名鼎鼎的薛御史气得说不出话来,也只有他这小儿子了。可惜的就是,没让朱明瞧见这一幕,也好出出他的恶气。
恰此时,陌山气喘吁吁地跑来,附在谢临川耳边道:“临安府署的刘爷,找您有急事。”
刘爷便是刘长风,长公主的故交,他的师父。
师父从来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他说有急事,一定是大事。
正好,薛家这点子破事,谢临川也懒得看,抬脚便走。
薛齐送了老父进去,却又追出来,拱了拱手:“今日薛某家丑外扬,让世子见笑了。”
谢临川停下来,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露出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施施然就往外边走了。
他突然觉得,这薛齐还有点儿意思。
那方才在杏花饭馆里……
他忽然有点儿后悔。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暂且不提。
冬月初二,王蕙娘从集市回到杏花饭馆时,怀里揣了一封信。
她四下一看。
虎子与团团两个脑袋凑在一起,蹲在河边的草丛边,看得认真,应是在帮女孩子捉蚂蚱。
她便掏出那信,低声道:“妹子,这是我汴梁的一个朋友写的信,你帮我念念可好?”
王蕙娘不识字,但因为常年做女侩,跟儿子苦学了些常用字,一般来说,信还是读得通的。
她见江清澜面露诧异,解释道:“我这朋友不识字,是找的街上的书信先生代写的。”
看着上面那佶屈聱牙的字,她揣测道,“我估摸着,是写字先生换人了。这次写的,我都看不懂了。”
江清澜听罢,就仔细看去。
抬眼是“嫂嫂”两个字。
底下第一段,写的是:问嫂嫂、虎子贤侄安。兄墓前松柏,亭亭如盖否?弟在汴梁,日日思君……
江清澜看罢,心道:
上次在松林村,蕙姐姐说,她的夫君是在战场死了的。全靠一个叫郑旺的结义兄弟,千里迢迢带了骨灰回来,才得以魂归故里。
原来就是这个人。
她道:“既然是虎子义叔来的信,怎不叫他来念?再去一封回信,一是全了他们叔侄情义,二也考较一下他的功课。”
说罢,便要唤虎子进来。
王蕙娘一听,脸色大变,忙摆手:“不不不,此事不可叫他知道。”
见江清澜好奇,她只扭捏道,“好妹子,日后我再与你细说,你先把这信念了。”
江清澜便细细再看。
这人东拉西扯的。大到汴梁换了什么府尹、开了什么酒楼,小到金明池的睡莲开了朵蓝紫色的花,拉拉杂杂的,写了个全。

![我貌美娇弱但碾压副本很合理吧[无限流]](/img/806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