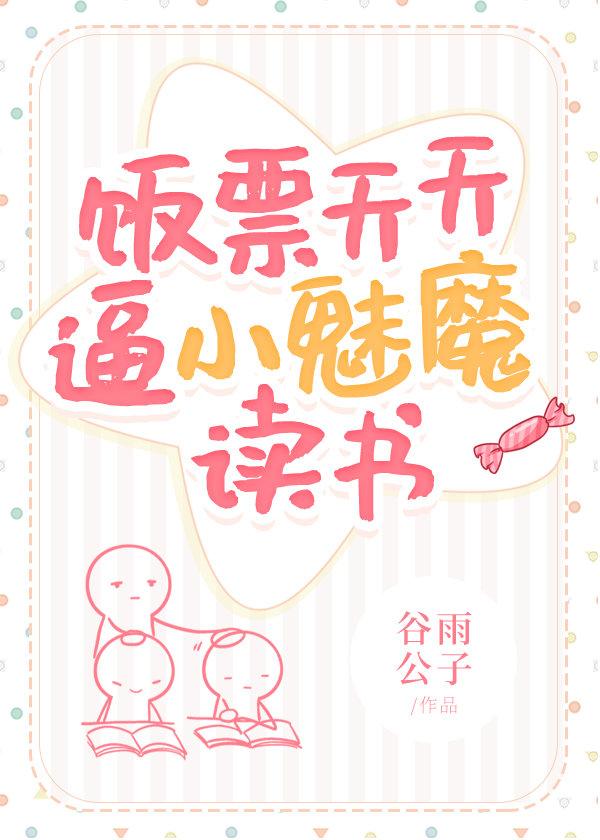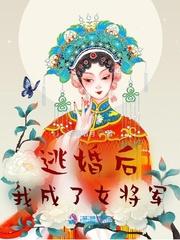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临安杏花饭馆(美食) > 4050(第2页)
4050(第2页)
自前日上了秋日菜单,供应的饭食一并更新,食客们越发来得殷勤。
白胡椒猪肚炖老鸡这种,到不了天黑就卖光了。后来的客人着急上火,埋怨道:“江娘子,你怎不多做些?”
江清澜只好赔笑:“抱歉抱歉,咱后院儿的锅只有那般大,装不了再多了。”
“不过,贵客请放心,铁匠铺子已在替咱们打新的大锅啦。”
客人只好怀着怨念走了。
然而,比猪肚鸡更火爆的,是羊肉。当时,江清澜并没有把“孜然焦炙羊肉”的竹牌挂出来,许多人却主动来问。
江清澜知道,历史上宋人极爱羊肉,甚至差点儿把羊吃绝。
“沙晴草软羔羊肥,玉肪与酒还相宜”[1],“寒羊肉如膏,江鱼如切玉”[2],这些写羊肉的诗,在宋代文学中比比皆是。
苏轼调任惠州时囊中羞涩,购入价廉的羊脊骨烹制,就有了流行至今的羊蝎子这道菜。
既然客户有需求,店家如何不应?
王蕙娘立刻去乡下买羊,先收一只来看看品质,如果反响好,再直接从货源地大量订购。
江清澜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打起帘子要往后院去。不曾想,张月娘正提着篮子出来,二人迎头碰上。
张月娘道:“娘子,早些时候,对面何家的春姐儿来过。说是买粥,却送了这么一堆萝卜。”
江清澜一看,竹篮里,白萝卜装得满满当当,个个成人拳头大小。
根须上沾着些泥,青青缨子上却还挂着浑圆的露珠。
看来,这萝卜是方从地里拔的。
她奇道:“哟,这么大一篮子,春姐儿提得动?”
张月娘细声解释:“她跟她妹妹抬着来的,两个人累得满头大汗。”
“我瞧着,篮子底下有些划痕。恐怕是姐妹两个抬不动,拖着走了一段路。”
“我留她们吃盏饮子再走,春姐儿只说,家里小弟弟睡着了,她们才出来的。得赶紧回去,免得他拉了尿、沤了屁股。”
江清澜心知,何家小弟弟才几个月大,日常是春姐儿两姐妹在照管。而这白萝卜,是何家夫妇还她卤鸡腿的情。
思索间,余光瞥见张月娘眉头微蹙,似乎很是忧郁。江清澜便知,她是由婴儿拉尿这些琐事,联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对一位母亲来说,没有比失去孩子更痛苦的事了。
月娘……实在太可怜了。
江清澜心中不忍,更不愿见张月娘沉溺于悲伤情绪中,便岔开话题:
“咱们的羊汤用什么配着炖,我正犯愁呢。这白萝卜来得正好,你快把它们切了,我马上来炖。”
说罢,迅速系上围裙,扎起攀膊。
其实,今天第一次买羊、吃羊肉,为着响应食客的需求之外,江清澜也另有一重打算。
购入杏花饭馆两间铺子,加上后面那块地皮,花了将近千两银子,但仍很划算。
尤其那地皮,是原来的主家生了重病,他女儿把地贱卖了,与父亲治病。
江清澜准备把地皮上的破屋子拆了,重建新院子。
这些日子,王蕙娘四处找人,便要开工了。日后,她们且得忙碌一阵。就先用这羊,吃一顿开工饭。
时近卯时初,晚市的人还没来,午市早已结束,最是清闲。
江清澜的羊肉大餐准备得差不多了。
便把腰上的围裙解了,在一边轻轻抖了下,挂在木架子上,招呼众人吃饭。
要说羊肉这等鲜美之物,各地有各地的吃法。
西北人爱烤,燕都人爱涮,川渝人则喜冬至喝羊肉汤,寓意一冬都不冷。
如今,他们有一整头羊,索性来了个大杂烩。
羊肉串是不可少的。
瘦、肥间杂的羊肉,一块块地穿在竹签子上,在小炭火上不停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