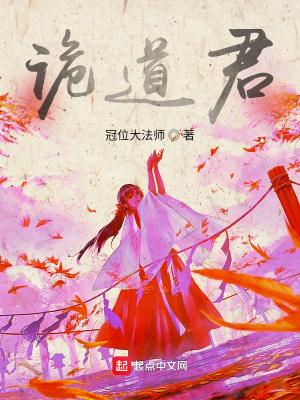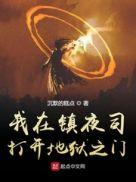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临安杏花饭馆(美食) > 3040(第39页)
3040(第39页)
“那……”王蕙娘斟酌道,“你娘家在哪儿,我们送你回去?”
张月娘摇摇头:“太远了,我回不去了。”眼中尽是凄然。
二人听罢,也无话可说,只得暂时将人带回江米巷。
王蕙娘取了一套自己的衣服,让张月娘换了。她的院子尚有空屋,便将人安置在此地。
张月娘梳洗打扮后,一张脸更显得柔美秀丽。只人仍是蔫蔫儿的,很少说话。
时近申末,门外大雨瓢泼。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串珠般不绝,敲打得街阴叮叮哐哐地响。
江清澜看着连天雨幕,暂绝了回杏花饭馆开张的心,举着伞,回了自家院子。
在厨房里忙活一阵,不多时,她又举着伞,提着个竹篮子,去隔壁院子。
见张月娘还盯着窗外大雨,怔怔然,她便道:“你肯定饿了,来尝尝这汆肉米线。”
张月娘听罢,杏眼瞪圆了,很是惊讶。
只见桌上放着个黄褐色的小砂锅。盖子一揭,热腾腾的白气滚滚冒出。
锅里,装得五颜六色的。
汤底上,浮满金黄色的油圈儿,像是散落的金箔——此乃肥美的老母鸡所炖就。
雪白的米线细长如银丝,在滚汤中舒展开来。露出汤面的,已裹了一层晶莹的油光。
绿豆芽是断生就捞的,韭菜段儿却纯由鸡汤烫熟,瞧着脆生生的,青碧可人。
猪肉片切得薄如蝉翼,被烫得微粉,灯盏窝儿一般蜷曲着。
一勺鲜红的茱萸酱聚在锅壁边,并未被搅散。
空气里,还有辛辣而芳香的气味儿,应该是放了胡椒粉的缘故。
江清澜笑道:“我听你有西南口音,应当爱吃这个吧?”
原来,方才在马车上,她便听了出来。又听张月娘说,娘家太远,就断定,她可能是西南人氏。
这汆肉米线,是云南文山的特色。此时,云南属于大理国,但西南人士普遍爱嗦米线。
江清澜读硕士时,学校北门边有一家十年老店,她经常去吃。
汤底鲜美、米线爽滑,百吃不厌。
尤其在秋冬冷飕飕的日子,嗦一锅米线,从口中暖到胃里,别提多幸福了。
她仿佛记得,汪曾祺的散文里写过一种“爨肉米线”。
“爨”与“汆”读音相似。但汪曾祺说,“爨肉米线”里放的是肉沫,她吃到的“汆肉米线”里,却是里脊肉片。
如此想来,这两种应该不一样吧?
如今,她做的这种,是按照学校外的那家米线店做的。
因为没有油辣椒等佐料,算不得正宗,但有那个意思就成。
她见张月娘点点头,便递过去一双筷子:
“这里面放了足够的胡椒、茱萸酱。你落水受了寒,要吃些发物,好发发寒。”
张月娘怔怔地看着,似乎有些惊讶。
为这锅热气腾腾的米线,为她的好心。
江清澜知她所想。当日,在建隆寺外,二人也是有缘。她便将此事复述一遍,总结道:
“那时,我十分困窘,父母都不在了,带着小妹妹在寺庙里寄居。多亏你买青梅,我才有本钱做生意。如今,算是挺过来了。”
“人嘛,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活着才有将来。”
张月娘一边吃着米线,一边默默听着。忽的抽了抽鼻子,眼泪串珠似的流下。
一碗米线吃完,她起身,扑通跪下,给江清澜磕了个头:
“娘子,多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是一时想不开,才做了傻事。既然留了这条命在,一定如你所言,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