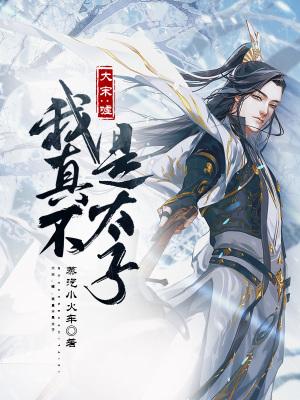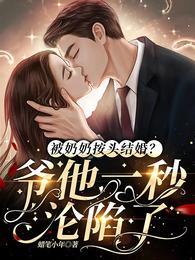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童养夫 > 第117章(第2页)
第117章(第2页)
于是众人纷纷打听苏壹喜欢什么好上门送礼,这一打听就发现苏壹此人了不得。
乡野农户出身的小子,凭着一手做墨的手艺,开铺子,办工坊,建商队,生意是做的风风火火,如今京都最火爆的棉绸庄也是苏壹的产业。
这还不算完,苏壹凭一己之力把契弟沈从仪送进了大儒李简正的门下,沈从仪九岁时被李简正收下做学生,之后考上状元,入翰林院。
苏壹此人不但有钱有眼光,还极其乐善好施。
在平安府时,就是有名的慈商,修路造桥、办学堂、建慈幼堂,还向寒门学子提供免费的阅书局。
这几年凡是平安府一带中考的寒门学子,就没几个不曾受过苏壹恩惠的。
因此苏壹明明是满身铜臭味的商人,却在读书人口中名声却极好,而且据说玻璃和镜子的方子也是苏壹提供的。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太子会把玻璃坊主事的职位给苏壹,但也有不服气想要暗中挑拨的,这半年来玻璃坊不知赚了多少钱,他们就不信苏壹不会中饱私囊,即便苏壹真清白,他们难道就不能按个罪名到苏壹身上?
可是当他们深入调查玻璃坊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经商模式。
玻璃坊的经营模式和所有人想的都不同,其中各种规章制度严明,各级管事、工人的职权和各项干活流程也极其严格。
不仅如此,他们了解到其实玻璃坊并不是苏壹的一言堂,在苏壹等管理层之下还分七房,分别为账房、生产房、采购房、营销房、开发房、质检房、人事房。
在七房之外,还有监管房和审计房,监管房的人隶属于内庭司礼监,审计房里则是户部的人。
可以说,整个玻璃坊是苏壹、司礼监、户部三方共管。
司礼监是皇帝的人,户部是太子的人,有两个大佬坐镇他们就是再想插手搅和也做不到,只能干巴巴看着玻璃坊卖出越来越多的玻璃,卖玻璃的大部分钱都流向了国库。
经此一事,苏壹无形中在京都站稳了脚跟,就连他名下的一系列私产也没人敢动。
有才华的人是掩饰不住自身魅力的,苏壹年轻多金,相貌不俗,且待人又和善,因此京中不少人仰慕他。
坊间还出现了很多关于苏壹的画本子,一度被人卖到脱销。
沈从仪嘴角抿直,生怕苏壹不和自己一块去固原。
在沈从仪心里,京都不乏一些人觊觎哥哥,他们或许是真的爱男风,又或许是想和男子相好来多得些钱财傍身。
那些人一个个诡计多端又能言善辩,苏壹向来心软,见不得世间苦难,万一被心术不正的人钻了空子,等自己从固原回来,家里说不定得多出来几个“哥哥弟弟”
沈从仪咬牙。
不行,绝对不能留哥哥一人在京都。
“我一去固原恐怕明年才能归家,万一哥哥忘了我怎么办?”沈从仪眉头微蹙,俊朗精致的脸上露出些许忧愁。
苏壹好笑的道,“你是去一年,又不是去十年,我记性还没那么差。”
沈从仪知道对付苏壹,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
一滴眼泪顺着脸颊落下,沈从仪抓住苏壹的衣角,“京都人才济济,比我更可怜可爱的男子多如过江之鲫,他们心思狡猾,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哥哥别往家里捡人好不好?”
听沈从仪这么说,苏壹有一瞬间心虚。
其实也不怪沈从仪这样想,早些年沈从仪去丰州书院读书时,在平安城的苏壹曾经就干过往家里捡人的事。
当时苏壹“捡”人时的思想很纯洁,他就是看那人可怜,而铺子当时又缺人,于是他就把人带回来当管培生培养。
结果谁知道,那人竟然喜欢男的,还搞半夜爬床这一套。
结果当然是被苏壹严词拒绝,秉着不能浪费劳动力的原则,苏壹就把人“发配”到了商队,去千里之外的铺子做工。
而且苏壹很唾弃这一套,他觉得那人是想从他这里走关系,意图更轻松的从管培生学校毕业,才会这样做。
苏氏商行内部管培生培养学校的竞争十分激烈,同一批次管培生内部配有淘汰制,不同成绩的管培生“毕业”之后,会被分配到不同岗位。
优秀管培生的起点,或许就是普通管培生这一辈子的终点。
这种事的发生让苏壹认识到了管培生学校的短板,于是就在内部发了通告,开会讨论批评,并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苏壹还记得后来这事不知怎的被沈从仪知道了,沈从仪还生了好久的脾气,索性事情发生第二天苏壹就把人“发配”了,否则苏壹觉得沈从仪真的会被气到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