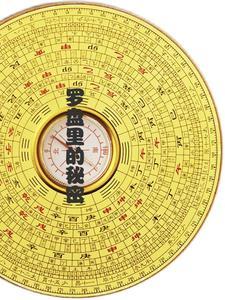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女主她一想退婚就会死 > 第225章(第2页)
第225章(第2页)
“只是我想着,人桑姑娘也不是什么囚犯,不管日后如何,她现在,也只是暂住在我们须弥宗,那位谢公子,是她的师兄,更是她的亲人,我们有什么立场不让他们二人相见?”
陆舜手里的动作一顿,而后抬手猛地拍了拍宗尧的脑袋,“我看你是疯了,宗主吩咐什么,我们便照做什么,用你想这些有的没的?”
宗尧却是鼓了鼓脸,他垂着眼,叹了一口气,看起来,竟是有些惆怅,“陆舜,我觉得宗主变了。”
他是盛逾的手下,盛逾吩咐的事情,宗尧向来倾尽全力去做。
可是同时,宗尧完全认同,也完全信任盛逾,他从不觉得盛逾做的事情有问题。
可是这次不一样,桑渡姑娘即便是宗主的未婚妻,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将人关在须弥宗上。
即便将人关在院子里不让人离开,可以说成是为了大局,毕竟那位桑姑娘先前孤身进入过沂梦涧,想来也是很不一般。
可那位谢公子,是人桑姑娘的家人,他们一群外人,有什么立场不让人相见呢。
听了宗尧这近乎大逆不道的话,陆舜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他低头继续给宗尧处理着身上的伤口,“宗尧,宗主平日里实在是溺爱你,这才让你如此无法无天。”
宗尧垂着眼没说话,只是看表情,显然是对盛逾这次的做法很是不满。
他认罚,自己玩忽职守,盛逾罚他是应该的。
可是,盛逾不让桑渡与自己的亲人相见,着实过分了些。
“宗尧,那位谢公子是桑姑娘的兄长,却不是桑姑娘嫡亲的兄长。”
“两人半夜相会,宗主不满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宗尧自然知道这个道理。
他眸光轻转,垂着眼,没说什么。
只是,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在感情一事强迫旁人,着实算不上什么君子之为。
沈慈昭第二日才发觉谢安淮消失了。
她去找,却没有半点下落,须弥宗的人也只推说不曾见过谢安淮。
一个活人,好端端的,竟是凭空消失了!
沈慈昭气急了,好在盛逾竟是遵守了承诺,让她见到了桑渡。
只是桑渡病了,病得很重,整个人都昏迷不醒。
沈慈昭于医理上并不精通,却也看得出桑渡的状况很是不好,躺在床上的人,单薄孱弱的仿佛一张纸片,随时会消失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