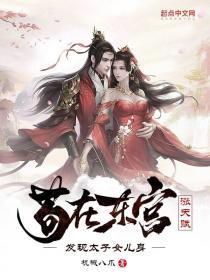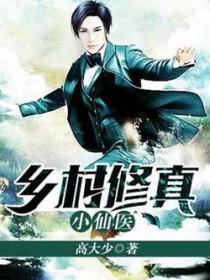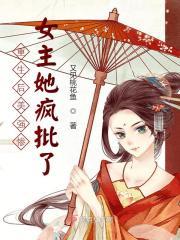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历史同人] 大明第一王妃 > 第71章(第2页)
第71章(第2页)
可,若东西当真在朱瞻基手上,他们又是如何知道的?
“我有一问,想先问问二位大人。不知二位大人,是从何处知道这篇词的?”
“我们是从宁王处知道的。”
解缙回了一句。
徐妙容更懵了,怎么又扯到了宁王?
“宁王手上拿着一沓纸,下官与解大人只见了这一张,听闻纸来自安王府,下官便猜到,是王妃所写。”
杨荣适时回了一句。
话音落,又有些后悔。
既然纸是从安王府来的,说不得余下那些纸上,还有更多的词作。方才他不应该走那么快的,他应该,把所有的词作都过一遍。
不过,眼下“文曲星”就在眼前,近水楼台,他少不得舔着脸,请安王妃再口述一遍。
“不瞒王妃说,下官已经将那首词完整记下了。”
又说了一句,杨荣果真完整地将整首词念出来了。
他的声音还算平静,可他的脸上,却写满了不平静。
徐妙容心里也不平静。
她很想说,杨荣,你可闭嘴吧。
她已经大概猜到了,东西是被朱权劫的。朱椿和朱权不来电,朱权为了“讨公道”的事,日日满腹心事。他没心思往兄弟们府上走动,又怕走动了朱棣忌讳,所以自来应天后,一直独来独往。
朱瞻基是朱棣的好大孙,见了好大孙,想起好大孙他爷爷做过的“孽”,朱权恶向胆边生,抢了朱瞻基的东西,也合乎情理。
只是,惹不起爷爷,只敢惹小朋友,朱权啊朱权,她该说他什么好。
眼下,听着杨荣复读机一样复读,她也不知道,说杨荣什么好。
有些心虚地看了朱楹一眼。
朱楹却好似听住了,他面上有一瞬间的异样。异样过后,却并不看她。
他问杨荣:“可是浑浊的浊?”
杨荣点头,眼中有一缕无言。
他就知道,安王读书多,是表面现象,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比之安王妃,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瞧瞧,他对文字是多么的不敏感。
“昔年苏子写下《念奴娇》,开篇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诉尽历史大势。而今一首《临江仙》后来居上,论旷达,洒脱,本王以后来者为上。”
朱楹“点评”了一句。
杨荣有些惊讶,沉默了一会,好半天,才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安王好古敏求,下官深以为然。”
你深以为然?
解缙撇嘴,前脚还看人家百般不顺眼,这会又瞧人家顺眼了?
想到刚才的问题还没得到答案,他忙看向徐妙容,问:“安王妃,你还没回答下官,这首词,你是何时写下的?写下这首词时,你又在,想些什么?”
其实这些问题,解缙本不想问的。毕竟,别人的伤心事,还是少提为妙。
可,身为大明文坛“暂时”的领袖,有时候他不得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文学鉴赏无法脱胎于创作时的背景,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不单是因为那些如珠玉一般耀目的文字,更是因为,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情感。
他僭越了,可他也不得不僭越。
他问了,徐妙容心中暗自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