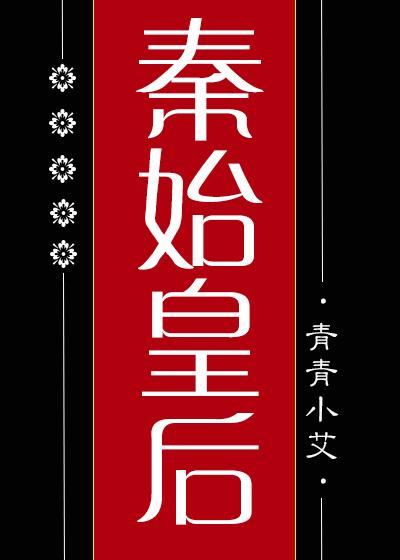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弯腰 > 3040(第5页)
3040(第5页)
对方的态度自然熟络,透着亲昵紧密,可赵怀钧实在没心,不太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见过她,这张脸也确实没在自己印象中留下分毫。
他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说:“有事儿,就没留。”
女孩子手肘搭上了车窗,低领的外衣随着动作不经意间展露出绝好风光,她柔声慢调地撒娇:“可是三哥不在就没意思了。”
黏黏糊糊的腔调如鸿毛一般,欲图轻轻撩拨男人的心。赵怀钧也不傻,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今夜她想跟着他走。
男人冷淡的眼里终于是慢慢碎出点儿笑意,手半搭在车窗,哂笑道:“不好玩?”
女孩摇头,樱唇微撅:“是三哥不在,不好玩。”
眼前这张脸满是讨好与刻意,可赵怀钧瞧着瞧着,莫名就想起两年前在上海那次的酒店里,半洇在池水中的墨色海藻,氤氲于水雾之下的轮廓,睫毛上汽着的未落水滴,还有水光潋滟中半露的玉体。
那些暖色的片段终汇聚在被水浸泡过后沾染着潮气的身子,和那双盈盈水灵的勾人眼睛。
她有种很直观很利落的美。
不必多加修辞,单单一个字便可完美形容。
赵怀钧第一眼就这么觉得。
后来两人纠缠不休,他又觉得,这江南水乡果然名不虚传。那把烟雨熏染过的清脆嗓子同他浪荡时,就像甜得过头的蜜饯果子,齁甜得人心战栗。
如同悬崖坠落谷底后,又再次被高高抛起,失重与超重无缝衔接,极速转换的瞬间血液沸腾,连肌肉都带着不自觉的紧绷。
纵使少时玩岁愒时朝歌夜弦,也再没有谁给过他那样激荡澎湃的感觉。
赵怀钧至今都记得有次带她去甘晓苒庄园时,他瞧她不爱打牌,便捞了人上附近登山徒步去。高从南他们对这项目没兴趣,所以一路上就他们俩。
只有他们俩,赵怀钧就多了些不正经。
他私下里喜欢拉着她闹,那嘴皮子偶尔淬了毒似的戳人心窝子,奉颐听不顺耳,闷头就往前走。可可走着走着,赵怀钧就见她路走岔了。他也不提醒,慢悠悠跟在她后面,直到她自己反应过来后霍然转身,气恼得骂他一句混蛋。
那模样漫染了桦树林的葱郁,看上去特别生动。
越临近三十岁这个年纪,人就越觉得时间可贵。更何况赵怀钧也不是那等毛头小子,见着什么姑娘就爱逗上一逗。
他就是觉得她特有意思。
比其他人都有意思。
这大概就是他那位好友调侃的——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就是可了惜了。
赵怀钧轻哂。
耳畔重复的呼唤将他的神智重新拉回来。
女孩子在他眼前轻挥了挥手:“三哥,想什么呢?”
赵怀钧一点点地收回目光。
还是那个女孩子的模样,只是形象在某人衬托之下逐渐变得寡淡。
不知怎的,忽然就有点意兴索然。
没意思。
应该说,这几个月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感觉就好像明明画好一副画却忘记点睛——总是缺了点什么,摸不着头绪也揪不出原因。
他拿过旁边的手机,给武邈打了个电话。
三分钟后,武邈从屋内小跑着出来。
“三哥,什么事儿啊?”
赵怀钧拿下巴点了点那姑娘,说:“人想回家,我也不顺路,只能劳驾你送送,回头再谢你。”
那冷淡模样同方才判若两人。
他这个人就这德行,待人和煦的时候温和有耐心,可若想冷下来,也许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样子看着比谁都绝情。
是改不了的劣根。
武邈愣了愣,转头去瞧身侧同样愣神的姑娘,姑娘眼圈似乎有些红了,瞧着赵怀钧没敢多说什么,只眼睁睁看着赵怀钧升上车窗,没留恋地踩下了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