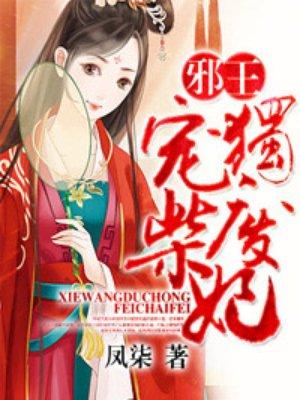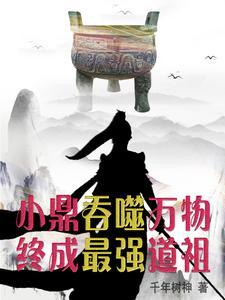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荡失 > 2030(第7页)
2030(第7页)
看封面的蓝色,应该是亨乐出品。最顶部印刷写着J。S。Bach。纸张边缘有轻微磨损,应该已经使用有些年月了。
其实现在学音乐的人,都已经普遍开始使用电子琴谱。iPad既便捷省时,价格还不贵。而实体曲谱总给人一种传统的、缓慢的、行将被抛弃的感觉,更适合当作收藏品束之高阁。
“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李絮读了一下封面标注的Urtext,有些好奇道,“你现在这么忙,还会经常抽空练琴吗。”
言漱礼掌着她的腰,垂着眼,淡淡答,“偶尔。”
“真好。”李絮毫不羞愧地笑了笑,“我指法都要忘光了。”
“你又不喜欢。”言漱礼不以为意,“忘不忘有什么所谓。”
“我怎么知道我不喜欢?”李絮似笑非笑,为自己辩解,“不喜欢不会学那么多年。我只是弹得差劲而已。”
“你口中随随便便说的喜欢。”言漱礼言语沉静,明明是晴朗日,却似隔着一层薄薄雨雾望她,“和实际上的喜欢,别人还是分得清的。”
这话隐隐有种指控的嫌疑。
古怪。微妙。又捉摸不定。
李絮有片刻哑然,不知道怎么接,索性维持着假惺惺的美丽作态,捏住琴谱的另一边装作认*真地低头看。
方才没有发现,在亨乐出版社的标识旁边,原来还有一个隽美流畅的黑色签名。
——LeonRosenbaum。
“Rosenbaum。”李絮下意识念了出来,略一思忖,有些犹豫要不要问出口,“这是你父亲的姓氏?”
言漱礼“嗯”了一声,没有表露出什么被冒犯的情绪,反而主动告诉她,“小时候在慕尼黑生活,就叫这个名字。”
“玫瑰树。”李絮轻声感慨,“好浪漫。”
言漱礼挑了挑眉,有些意外,“你知道。”
“我们学校有位来自柏林的教授。”李絮说,“也姓Rosenbaum,她给我们解释过含义。”
言漱礼静静看着她,任她接过那本琴谱,“在德国不算什么罕见的姓氏。”
“LeonRosenbaum。”李絮却感觉特别,手指抚过这行陈旧字迹,喃喃地完整念了一遍这个被舍弃不用的名字。
思及他父母遭遇空难的旧事,以及他小时候曾经患过的失语症。心绪难免有些复杂。最后还是装作不知情的样子,微微拎了拎唇角,“玫瑰树下的小狮子。好可爱。意外地很衬你。”
言漱礼没有对这个评价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揽她的手臂稍微紧了紧,很有些不习惯似的,不动声色将脸别到另一个方向去。
“除了我妈妈,只有你会这么说。”过几秒,他低低道。
不像多高兴的样子。也不像多感怀的样子。只是面无表情,平静而平淡地实话实说,仿佛一本等待翻阅的旧书,没有明确禁止她继续探究自己的过去。
好奇怪。
在这平平无奇的一瞬间,日光照耀着空气里的微尘,眼皮间涌动着轻盈的气泡。
李絮倏忽感觉自己被一种明亮、奇异而陌生的情绪,哐地一声击中了。
她分辨不出那究竟名为何物。
只知道自己本能地想要抓住它。
“反正我还要等颜料晾干——”于是她脸不红心不跳,在情不自禁的冲动之下,撒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Leon,我可以给你画幅肖像吗?”
第23章担心你会融化。
23
李絮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正经画过油画肖像了。
事实上,自二十世纪末以来,意大利和法国那边画油画的人就明显变少了许多,画得好的大师更是寥寥无几。
即便是采取了油画这种形式,艺术家们多数也会融合新鲜的技术、材料与视角,倾向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尽量避免古典的写实标签。
如今一般公立美院都不会再开设油画技法的课程,除了读绘画方法论的,其余只会有几节理论课,再加一点点实验课。教授不会在技法上指导你,也不会在风格上限制你,只会鼓励你随心所欲地使用各种媒介与表现手法。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更是格外注重当代艺术的发展。
李絮选的新语言表达专业,在本科的时候,入学考试重心还会稍稍侧重于从古希腊到新古典主义这段艺术史,作品集也会充分考量学生的基础练习与理论水平。
到了研究生时期,重心则完完全全偏向从立体主义至今的这段当代艺术史,作品集也更加看重装置、概念、行为等方面的创造力。
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受当代艺术的脆弱性影响,李絮的审美,总是介于一个岌岌可危的矛盾平衡点。
![流放后嫁给失忆将军[重生]](/img/1532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