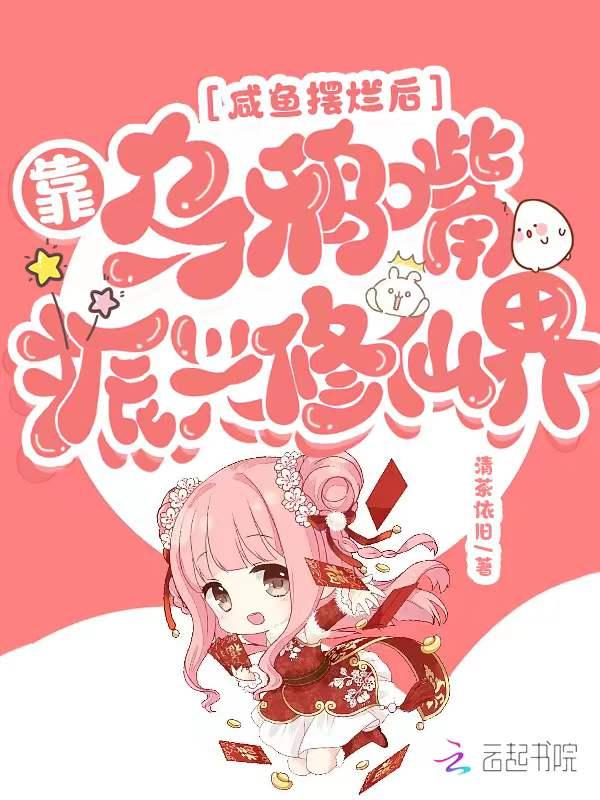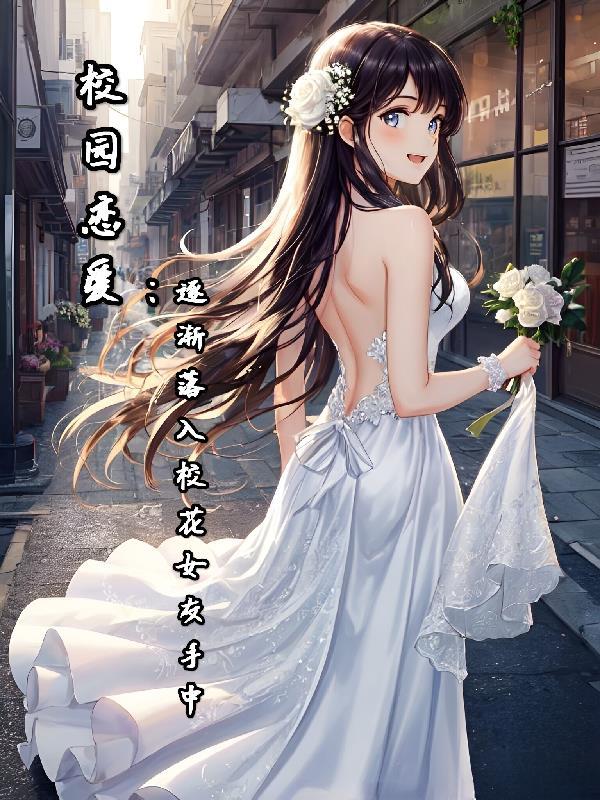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动春心(重生) > 190198(第8页)
190198(第8页)
“既然如你所言如此小心,为何贤嫔还会出事!”新帝蓦然看向她,神色晦暗不明。
施姑姑被吓了一跳,哪还记得为自己辩解,只喃喃重复道:“陛下饶命,陛下饶命。”
她失了心神,眼见再问不出什么来,新帝愈发不耐。
他揉了揉突突直跳的眉心,抬手就要发落施姑姑,却见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忽然扬声道:“陛下!老奴想起来了,三日前娘娘从惠妃那得了一盒胭脂。早前太医每日请脉都无大碍,可在那日之后,娘娘就时常腹痛难忍,如今想来,定是胭脂的缘故!”
听了施姑姑所言,盛锦水只觉心惊。
来时福德就已在萧家言明胭脂之事,如今新帝却装作若无其事,让太医又将诊断细说了一遍,随即才是施姑姑陈情,道明原委。
帝心果真深不可测,贤嫔小产,方才还在内室疼得死去活来,祈求新帝为自己主持公道。
再转眼,新帝就给她身边的管事姑姑设局,显然是不信她。
“福德。”
新帝一声吩咐,福德取出瓷罐,上前问施姑姑:“仔细瞧瞧,这是不是你说的胭脂?”
施姑姑忙直起身来,凑近仔细端详。
胭脂已被用过,边缘落了些细粉。
再看瓷罐,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开口道:“能否让老奴瞧瞧罐底?”
福德回头请示,见新帝点头才将罐底露了出来。
不老春用来装胭脂的瓷罐都是定制的,底部留有红泥印记。
施姑姑一见那印记,就忙不迭地点头,“这就是娘娘从惠妃那得来的胭脂!”
闻言,福德收回胭脂,又转递给太医。
太医双手接过,仔细端详其色泽,又抹了些在手背上,随即道:“陛下,胭脂里确实用了红蓝花。”
“惠妃,你有什么话说?”新帝沉声问道。
惠妃一怔,忙出声为自己辩解:“贤嫔确实从臣妾这得了胭脂,可绝对不是红蓝花的!”
见她如此笃定,新帝皱眉:“你殿里的宫人招认,金姑姑受命去过不老春。后来盛氏入宫,不仅亲自为你上妆还曾言明,胭脂中的红蓝花有活血化瘀之效。”
“陛下,臣妾是命金姑姑出宫带回不老春的胭脂,萧夫人也确实受臣妾召见入宫。”惠妃缓了过来,到底是世家出身,初时的惊惶过后就立刻冷静了下来。
她没抬头,但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中州城里无人不知,让不老春声名鹊起的就是红蓝花胭脂。且又有萧夫人多次提点,就算臣妾想谋害皇嗣,也不会蠢到亲手将胭脂送到贤嫔手里。更可笑的是,施姑姑口口声声说自己照料精细,既然精细又怎会不知臣妾的胭脂出自不老
春,而不老春里最出名的就是红蓝花胭脂!”
听完她的一番辩白,盛锦水却是愣住了。
分明有更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惠妃却避而不谈。这般一唱一和,她与新帝到底在筹谋些什么?
“盛氏,此事是否真如惠妃所言?”新帝问道。
盛锦水摸不准两人在打什么哑谜,如实回道:“确实如此,还有一件事想问过施姑姑,陛下面前还请如实作答。贤嫔娘娘真是在三日前感到腹痛不适的?”
没想到她有此一问,施姑姑眼神躲闪,脸上露出一丝几不可察的迟疑神色,随即笃定道:“正是如此,太医可以作证!”
“那就怪了。”盛锦水看她一眼,“蒙召进宫时,民妇确实带了胭脂,可其中并未掺入红蓝花。至于惠妃娘娘着金姑姑采买的那罐,前次进宫时民妇去而复返,已讨要回来,如今正放置家中,陛下命人一看便知。”
施姑姑一愣,顿时慌了手脚,忙跪行上前,指着盛锦水咬牙道:“陛下,方才那些全是这毒妇的推诿之言,她随意取出一罐就能说是从宫里带出来的,不能信啊!”
毒妇这形容一出口,盛锦水还没反应过来,萧南山就已忍不了了。
他何等聪明,怎会猜不到几人打的机锋。
可新帝有心算计,他却不想再做筏子,起身一脚将人踹翻,直视新帝道:“陛下胸有丘壑,又何必在此打哑谜。”
萧南山这一脚收着劲,就算盛怒之下,他也只是想让对方闭上满口污言秽语的嘴而已,并未想过真的踢中。
可没想到施姑姑看着蠢笨,实际异常机敏,就地滚了一圈,哎呦哎呦地痛叫出声。
又是一阵珠帘脆响,内室有人快步走了出来。
这次来的是贤嫔极为信重的宫人,方才一直在内侍奉。
见此情景,她先是吓了一跳,随即跪下,带着点哭腔道:“陛下恕罪,姑姑也是为娘娘着急,这才口不择言。娘娘累得昏睡了过去,方才醒转,不曾护好腹中胎儿,娘娘痛心自责,也请陛下顾全龙体,万勿动怒。”
新帝扶额,颇觉头疼,一个两个都太有主意,让他不得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