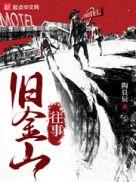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十里人家 > 4050(第20页)
4050(第20页)
码头上的船工、纤夫、来往客商,甚至附近镇上的居民,都成了茶棚的常客。
白潋琢磨着增加了新口味,都颇受欢迎。
不过,她也需要帮手。
茶棚生意蒸蒸日上,仅靠白潋和两位轮流售卖的妇人已然不够,尤其在高峰时段,收银记账常显忙乱。
白潋直接在码头显眼处贴了招工告示。
不过一日,便有人前来应征。
白潋选定了一位名叫林秀的年轻女子,林秀曾在镇上一家小布庄做过几年账房,因布庄歇业在家,为人沉稳,算盘打得精熟。
林秀次日便来上工。
她性子沉静,做事却极有条理,算账收银一丝不苟,招呼客人也温和周到。
林秀一到岗,两位卖茶的妇人得以专注递茶与清洗,效率大增。
白潋肩上的担子顿时轻了不少。
这天午后,白潋在茶棚忙活完,走到正在岸边查看“百福号”装货情况的伏棂身边,“这边事情都理顺了。咱们是不是该找个时间回村里看看了?出来好些天了。”
伏棂闻言,放下手中的货单,抬眼望向十里村的方向,“是该回去了。”
两人交代了石燕几句,第二天便驾着马车离开了河沿镇。
离开之前,白潋特意采买了一些东西。
回到十里村伏家小院时,已是傍晚时分。
“小姐!”小音从堂屋里快步迎了出来。
她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喜悦和关切,先是对着伏棂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您可算回来了!路上辛苦了!”
随即又转向白潋,也行了礼,“白当家安好!”
伏棂温和道,“嗯,回来了。家里可好?”
“都好都好!”小音连忙应道,“小姐的房间奴婢天天打扫,您爱喝的雨前龙井也备好了。”
她说着,关心道,“小姐,您瞧着清减了些,可是累着了?”
白潋在一旁笑道,“小音还是这么细心周到。”
“白当家,您也快进屋歇歇吧。灶上温着莲子羹呢,奴婢这就去端来!”
李大娘听到动静,也笑呵呵地从灶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小姐,白姑娘,可算回来了,一路辛苦!快进屋歇着,晚饭马上就好。”
小音抿嘴一笑,“小姐,白姑娘,你们快尝尝这莲子羹,清甜着呢!”
……
两人回来的消息,传了出去,许多人都来了。
翠儿似乎又长高了些,多了几分书卷气和沉稳,笑着问好,“伏夫子,白姐姐,你们回来啦!私塾那边孩子们都挺好的。”
去年冬天一过,捱过来的老人家又恢复了一星半点的活力。
三婆婆、村长他们都来了,白潋几乎一个月都不在十里村,他们还怪想她的。
这几乎是白潋离十里村最长的时间了,从小到大,白潋都是在这些老人眼里长大的,听说她生意越来越好了,几个老人也为她高兴。
给王婶儿的东西,是一个崭新的捣药钵,配着一根光滑结实的药杵,打磨得十分光滑。
“哎呀!这…这太实用了!”王婶惊喜地摸着厚实的钵身,“我那旧的都裂了缝,正愁没个趁手的捣蒜泥、碾香料呢。小潋破费了!”
“不破费,一点心意。”白潋笑着,“好用就行!”
她和伏棂这段时间不在十里村,两家都没什么人,伏家人只有小音一个,狗只有小汪一只,劳村里这些熟人顾看顾看。虽说伏家家大业大的,估计没什么人会欺上门来,可小音若有些事需要帮忙,也是劳他们搭把手。
王婶捧着捣钵,笑得合不拢嘴,“好用!肯定好用!”
给村长的是新出的、专治老寒腿的艾草热敷药包,厚厚一摞。
……
小音在一旁忙前忙后添茶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