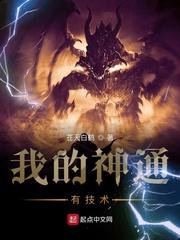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厌世女巫隐居手札 > 4050(第17页)
4050(第17页)
可这能责怪她吗?被周围环境裹挟的小孩,无法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怪玛蒂的妈妈没能嫁给一个好人吗?可这个丈夫本也不是她挑选的。
那怪谁?怪从玛蒂出生前就去世的外公外婆吗?
他们当时选择科里作为女婿,是看中他的老实,觉得以自己的能耐足以拿捏他,将独女嫁过去,以后日子好过。
谁料一场意外让两位精明的老人去世,留下单纯的独女带着巨额的财产,遵从父母定下的婚约,嫁给科里。
这又怪谁?怪命运不公,还是玛蒂的外公外婆将她的母亲养成了不谙世事的性子,还留下了令人觊觎的财产?
他们从未想过让玛蒂的母亲继承财产,当初得了一个女儿,他们想着以后总有男丁,就任由女儿长得天真烂漫,谁料往后经年再没有生下另一个孩子。
等后悔时,女儿已经长定型了,年纪了大,教也教不会,只好给她找一个夫婿,盼望她早日结婚生子,好培养外孙。
可未来如何,并不会以人的意志发展。
一切不如人意,难道最后只能责怪于命吗?
不尽然。
假使玛蒂的外祖不受外界影响,细心培养自己的孩子,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假使玛蒂的母亲坚强有主见,能在第一次发现丈夫赌博时狠心断掉他的钱,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假使这个世界给予女性更多宽容,允许她们有更多选择,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可以晚婚甚至不婚、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
有这么多可能,这么多生路,偏偏玛蒂的母亲没有选择,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死路。
从始至终,有选择的都只是他人——比玛蒂母亲更具有“权势”的他人,但他们的选择始终有利于自己,并未站在玛蒂母亲的立场考虑过。
作为众多女性缩影的玛蒂母亲,唯一能选择时,也是选择牺牲自己,为儿女谋取前程。
她或许还有其他选择,但她已经习惯了被索取,无法再接受另一种不用奉献的选择。
去世的这一年,她才三十五岁,还很年轻,她肯定有过很多害怕、绝望的时刻,但她定是怜惜被自己带来世界的三个孩子,所以撑了很久,但可悲的是,她的孩子没有一个记得她原本的名字,只能让她被禁锢在名为“科里”的牢笼,至死无法挣脱。
那一天,玛蒂哭了很久,哭过后她做了一个决定:不在母亲的墓碑上称呼她为“科里夫人”。
她请丈夫回珍珠小镇和母亲的老家,向可能知道的人打听母亲原本的姓名,假如始终无法得知,她便只会在碑上刻下“伟大的女士——子女玛蒂、马克、玛丽刻”。
敬她的无私奉献,敬她半生孤苦流离,敬她的坚韧,不以母亲的身份为禁锢,仅以她个人,她自己。
她的种种细腻心思没人懂得,包括弟弟妹妹,只是他们觉得玛蒂已经做了决定,就不愿反对让她不开心。
玛蒂心中的孤独日渐浓郁,但她知道一个人一定会理解她、支持她。
那人就是邦妮。
确实,当二人再见,玛蒂将自己的想法一一说给邦妮听,她展现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并承诺回去后向母亲米娅打听。
当年他们两家做邻居好几年,米娅或许会知道些什么。
除了母亲,玛蒂还向邦妮倾诉了很多。
这些年,她和丈夫感情很好,但直到生下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后,她才彻底放下心来。
也直到做了母亲,她才能体会到几分自己的母亲,当年心中的种种苦楚。
同时,她也无比担忧自己的孩子未来的前程,可她除了担忧,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的一切都仰仗于父亲。
而无可避免的贵族交际,也把玛蒂·科里,变为了男爵夫人。
没有人会喊她玛蒂:丈夫唤她亲爱的,弟弟妹妹唤她姐姐,孩子们叫她妈妈,她应该知足的,可偶尔心情不好时,她还是感受到了内心巨大的空虚。
虽然吃喝不愁,但她现在远没有从前在明纱小镇做纺织工时有成就感。
面对玛蒂的迷茫,邦妮并没有安慰她想开点、过段时间就好了,而是问她想不想在索伦城开一家成衣铺子。
玛蒂一愣,问她什么意思,邦妮便说:“我的姨妈劳拉,一直有扩大成衣铺子的打算,你们也熟悉,若是想,我帮你问她要不要跟你合伙。”
玛蒂心动了,但有些犹豫,不是顾忌什么,只是对于陌生事物有天然的恐惧。
她熟悉纺织,却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她担心自己会做不好。
“我、我能行吗?”
邦妮鼓励她,“当然可以!你都能自己一个人在明纱小镇生活这么久,还能在你母亲走后把弟弟妹妹带得那么好,嫁给埃里克后,与贵族交际也滴水不漏,你都不行谁能行?”
故意奉承的话逗笑了玛蒂,她终于点头答应了。
不过邦妮还提醒她:“既然你和埃里克感情好,那你心里的想法也要及时和他沟通。不管是之前觉得不适应,想要有人能够喊你的名字,还是现在要做生意。夫妻之间嘛,有商有量的才不伤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