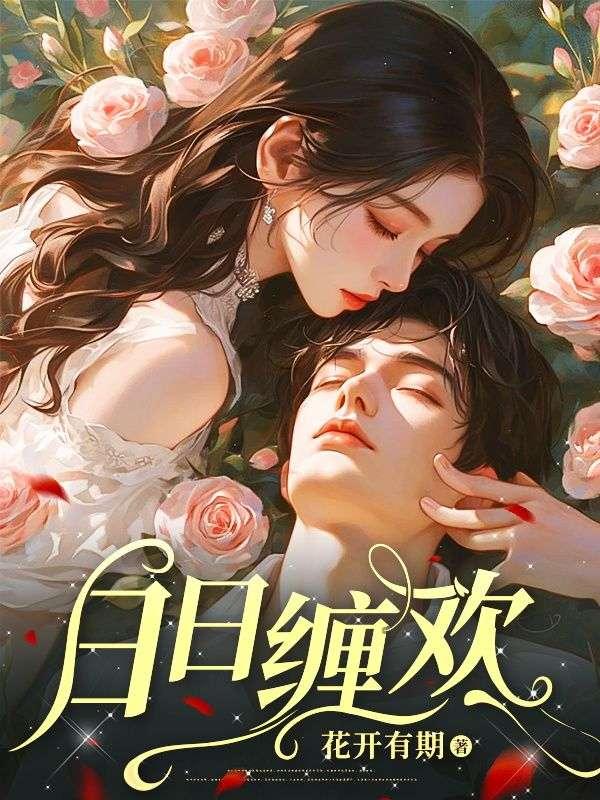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横刀夺取 > 6070(第12页)
6070(第12页)
等到了他的老房子,去不去庆成市又是另一回事——坚决不去,买了票也不去。
一个要去,一个不,师徒俩出院后必然要闹,谁也不退步,都固执,没得商量。
二爷放话,除非死了,或者现场吊死在房梁上,否则绝不踏出这间屋子半步。
去啥庆成市,还不够麻烦么,都没多少活头了,还能不能消停点了,让他过过清净日子不成吗,搞那么多名堂累得慌。
软硬兼施都不行,即便陈则差点跪下相逼,二爷硬骨头,又气又急,教训道:“没出息的东西,还嫌老子折寿少了是不,为这点事你一双膝盖就软了,你别想绑架我,趁早放弃,把老子惹毛了,以后你别想再进这里半步!”
骂没用,陈则充耳不闻,不答应不作罢。
二爷抬起胳膊,可终究没舍得打,没料到陈则会这么做,拿着束手无策。
闹得难以收场,僵持不下。
迟一些,贺云西拽了把陈则,二爷进去了,贺云西站二爷那边,却不与陈则统一战线。
“你别管我。”
“够了,可以了。”
“不关你的事,你不要掺和。”
“一定要这么讲话?”
陈则薄唇紧抿,不讲了。
一会儿,贺云西看着他,倏尔说:“他已经去过庆成市了,在那边做过检查的。”
陈则怔了怔:“你怎么知道?”
“我带他去的。”
“……”
“刚回这边那阵子,我带他去过了,跑了两家医院,不止去了庆成,后面还去了海市。”
上几次送二爷去医院的人,也是贺云西。
没什么好隐瞒的,陈则迟早会猜到,二爷身边除了他,唯一能帮得上忙的年轻人就是贺云西了,他在医院里都那么问了,二爷不讲,贺云西自己说。
现在再去庆成市没意义,注定白跑一趟。
二爷不想去,是因为已经去过了,不告诉陈则,是怕他怪贺云西——究其根本,问题不出在贺云西身上,不是他有意瞒着,是二爷千方百计不告诉陈则,让贺云西别讲,一块儿瞒着。
二爷生病这事,不单单贺云西知晓,老友们,诸如邹叔张师、曾光友等等,所有人都一清二楚。
原先陈则帮邹叔他们瞒着大邹,说那种话,其实曾光友也对他讲过类似的,只是他不上心,没深想过,忽略了。
当局者迷,他和大邹都一样。
所以二爷也为陈则铺路,最初拉下老脸组饭局讨好贺云西,给他找工作,后来自作主张收方时奕给的高额分手费,直至在五金店定下。
陈则比大邹争气,省心,没让人失望,不枉费二爷辛苦规划。
“不要折腾他了。”贺云西轻声说,夜色遮了这人大半的脸,看不出神情,嗓音有些低沉,带着不合时宜的理智克制。
……
二爷气够了再出来,房门口的空花盆四分五裂,陈则已经离开,只剩半边木门摇动,另一半报废烂地上了。
二爷瞪眼,关心贺云西:“他打你了?”
贺云西摇头:“没有。”
二爷斥道:“他这狗脾气,谁能受得了,气性那么大,真是……”
第66章心意“你把自己搭进来就行?”……
出了门没走彻底,陈则一直在附近打转,吹够冷风了,大晚上浑身上下被冻得冰凉,十点前又折了回去。
再如何憋火,还是不会就那样任性地置气离开。
清晨,花盆碎片被清理干净,换了个新的放台阶边侧下方。门修好了,还上了一道新锁。
陈则候堂屋里,待二爷睡醒了,倒杯热水,连带着把昨天医院拿的药推上前。
二爷勉为其难依从,吞药,一杯水全干了,喝完伸舌头张开嘴,堪比监狱检查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