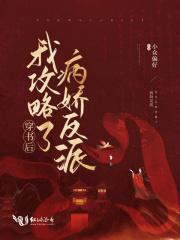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卷王的六零年代 > 130140(第12页)
130140(第12页)
而他们大河以南的河堤呢?堤面宽度仅有一米五到两米左右,并不具备形成的功能,而是作为防洪水的堤坝在使用。
这在许明月看来,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其实在最早建造堤坝的时候,既然数百里的堤坝都建了起来,又何必少了临河大队通往炭山的这一小段堤坝?
这要这条堤坝也建成堤面宽度六七米的路面,直接就把大河两岸给联通了呀,纠结大河以南几十上百年的行路难的问题,就解决了呀!
炭山因为巨型煤矿的缘故,早早就通了路,后来的省道便从水埠公社通往炭山,使得炭山的交通十分发达。
而河对岸的临河大队呢?是年年盼建桥,日日盼建桥,盼了几十年,路没从堤坝上通过,反而从石涧大队的深山里,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出去了。
搞的后来临河大队发展的还不如山里。
因为只要临河大队到炭山这条距离最近,最便捷的路不通,临河大队就永远被困在大河的中间,前面是河,后面是山,永远隔离于世界之外。
即使后来借了五公山公社,从山的那头通了路过来,可山里本就山路十八弯,山路深深不知深几许,更别提通到临河大队这里,中间的建筑材料也不知道被贪污了多少,在山路路口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五米宽的路,修到里面,只有两米宽了,会车都做不到,一旦有车子从对面驶来,另一辆车就得退到田地里去,等对面的车过去后,才能继续行车。
这严重阻碍了临河大队经济的发展。
现在这时代,正是堤坝刚开始修建的时候,既然如此,何不将这一段堤坝改一改,直接把临河大队和河对岸的炭山的路打通,今后临河大队的人出行也不至于那么困难,也省的临河大队这边的人,祖祖辈辈心心念念都是能修座桥。
许明月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将一道道修改后的堤坝路线,清晰的画在黑暗上,说:“一旦通往炭山的这段堤坝能建成,到时候和平大队,建设大队,我们大河以南沿河的所有大队,甚至是更深远的大山里的大队,都可以通过我们临河大队的这段堤坝走出去,联通竹子河两岸的经济,把大山里面的经济一起带动和开发出来!”
第138章 第138章先前许明月提出这个方……
先前许明月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更多的是注重那一万多亩可以开采出来的良田,他们还真没有这么前瞻性的经济眼光,毕竟前世的堤坝修建,就是直接把大河以南这块地,修成了一块绝地,还是到千禧年之后,才给村子通了路,还是那种窄到完全无法会车,只能让一辆车勉强通行的水泥路。
许明月这个堤坝改建计划,除了解决了那一万多亩地的灌溉问题外,同时还解决了两岸的经济问题。
这是过去从未有人从大河以南这块绝地的位置想过的。
邻市后来倒是建起了一座联通两岸的长江大桥,可惜这座长江大桥距离他们这边还是太远,倒是拉起了邻市的两岸经济,却对他们这边的经济毫无作用。
就连原本只以为是多开辟出来一万多亩田地的县委书记、县长和负责河堤规划的水利专家们,都正经了神色。
许明月没有说要截留一段竹子河给临河大队当养鱼场的事,毕竟这是私心的事,事情可以做,却不好说,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起这个问题。
“书记和县长、周副县长、孙副县长都知道,我们临河大队之所以能在三年灾害当中,还有足够的水灌溉农田,就是因为我们大队提前从竹子河方向挖了一条大河沟,解决了灌溉问题,如果我们的河堤沿着石涧大队方向,一直通往到五公山下这块大片的土地,解决灌溉问题,也只需一条大河沟就可以,但如果不只是河沟,而是河道的话……”
她用粉笔将河沟加宽了些许,说:“只需将大河沟稍稍加宽三到五米,就可以同时解决五公山公社,乃至五公山更深处大山里的山民们的交通问题。山里的山民可以通过五公山的河道,近可直达五公山公社街道,远可以通过河道进入竹子河,抵达水埠公社与邻市……”
许明月话音未落,就有人摇头反对说:“不妥,现在出门都要开证明的,哪里能让人随便走出去?那样不行。”
许明月一顿,她完全从后世经济角度,才提出这个方案来,倒忘了这个年代间谍特务横行,为了防止间谍特务们的行动,将这个时代的人都限制在本地,随意不可出远门的事了。
许明月话音一转,笑着说:“倒是我想的差了,只想着如何为我们大河以南的百姓谋福祉,想要拉动两岸经济,倒是没往深了想,还是领导想事情周全细致。”
剩下的话她就不说了,把话头交给了最高领导的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听完许明月对这段堤坝的规划,对周围旁听的专家和其它公社的书记们说:“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听完小许同志的发言,你们有没有建议和补充的,一起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搞,要怎么搞,说个具体的方案出来!”
吴城周边的几个公社的领导完全没想到,这个水埠公社在过去三年才搞出来一个蒲河口农场后,这么快就又搞出来一个大动作,上次是六七千亩地的农场,这次干脆是开辟一万多亩地的农田,彻底解决以五公山公社为中心,下面一大片生产大队田地少,土地无法灌溉问题。
他们之前就听说蒲河口农场就是一个小姑娘提的方案,许金虎施行搞出来的,看着年纪轻轻的许明月,又搞出这么大一件事,想着提出开发蒲河口农场方案的人,十有八九也是她了。
就有人提意见说:“既然是解决灌溉问题,那就像临河大队那样,挖一条河沟也就行了,要是河沟搞太大,劳民伤财不说,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不晓得多少年才能把那条所谓的河道开发出来。”
又有人说:“还有在原有的河堤上改道,连接大河两岸的事,现在河上有船,两岸原本就联通的,多这一道堤坝,不晓得要多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又是劳民伤财的事,根本没必要!”
“就是,马上就要春耕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多修一道堤坝,这堤坝的修建原本就是各位专家提前设计好的,哪里是能说改就改的?你们河南有船,根本没必要把河堤修的那么宽,我们大河北边是没办法,才修的这么宽,要是我们也能修窄一点,求之不得!”这是完全只看到眼前利益,看不到河堤修成省道后,对他们公社和下面大队经济影响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
只说一点,他们大河以北的人,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全部通了柏油马路,他们大河以南,零五年左右,还在靠着两条腿,艰难的从狭窄的提拔上走上两个多小时,艰难穿行。
此时人的思维是极受当下的思想眼光所限制的,尤其是在一些政策的限制下,原本被许明月说动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当下都犹豫了,问周副县长和孙副县长说:“老周,老孙,你们俩都是从水埠公社上来的,对水埠公社你们是最熟悉的,你们俩怎么看?”
孙书记是亲眼去过临河大队瞧过的,知道三年前的临河大队是怎样穷困潦倒,与周边其它的和平大队、建设大队、石涧大队没有太大区别,皆是一派的资源匮乏,也是清楚明白的知道,在这三年灾害当中,江天旺和许金虎两人,是如何带着临河大队,从原本贫瘠落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养活无数灾民的产粮大队。
周边公社、大队,乃至全县、全市、全省范围内,饿死了无数人,唯独临河大队,不仅没有饿死一人,每年还上交了几百万斤的粮食,让他们省在众多受灾各省中脱颖而出。
不然他和老周是怎么一下子从公社书记、生产主任升跃成为副县长的?
就连原本的县委书记、县长,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不都临河大队和蒲河口农场产出的粮食而高升了吗?
孙书记自认许金虎和许明月两人都是福将,便说:“临河大队过去三年做下的成绩大家伙儿也都看到了,那个有名的圈河滩为良田的计划,就是小许同志提出的,现在临河大队每年两季,为临河大队多产出一百多万斤的粮食,蒲河口农场的七千多亩田地,每年两季更是能产出几百上千万斤的红薯,为我们省的饥荒问题出了大力!”
他顿了顿,目光看向在座的其他人说:“现在小许同志再次提出,解决五公山公社山下这片土地的灌溉问题,一旦这片地的灌溉问题解决,到时候我们吴城继蒲河口农场后,将再次出现一片产粮之地,我想这给我们吴城所带来的收益是大家都能看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