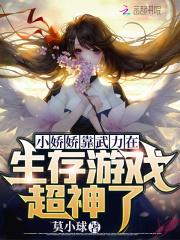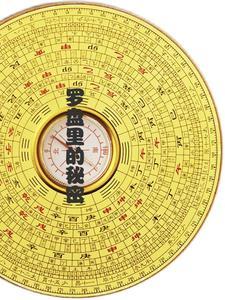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月与砂 > 相遇(第1页)
相遇(第1页)
灰色的砖墙上有一扇小小的方窗,被两根铁栏分成三格。清晨淡薄的日光从窗口落在生锈的铁镣上,反射出模糊的银光,像一片未散尽的月色。
艾玛已经醒了,或者说,因为寒冷,本就没敢睡着。
每年都有很多人会死在这样的低温里,死在多一堆稻草、多一条毯子就能抵御的冬天的尾声。
她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布裙,站起来时裙摆甚至不能覆过膝盖,但那些看守们很满意,认为这样简陋的打扮确实藏不起什么能撬锁的小玩意儿。
日头开始升起,窗外遥远的人声跟着逐渐热闹。门锁上的铁链哗啦啦响了一阵,昭示着这座奴隶市场今日的营业开始。
隔壁哭了一晚上的女孩还在断断续续地呜咽,不知道是想到了家人、朋友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艾玛抱着膝盖,听着她沙哑的泣音发了好一会儿愣,什么也没能想到。
艾玛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小商人,和做这行的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夜暴富进而加官进爵的野望,但始终没能交到什么好运。
他所有稳定的资产不过一间小屋、一驾马车、一位干体力活的男仆和两位处理家庭杂务的女仆。而艾玛的母亲是那个家里唯二的女仆之一。
也就是说,她是个不光彩的私生女。
家里的夫人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她,以施恩的语气,强调艾玛还能隐藏私生女的身份,作为女仆、奴隶、她父亲的资产之一,留在这个家中不被遗弃的原因:
一则当然因为夫人的宽容大度,二则艾玛的母亲极力恳求,三则——艾玛有一双天生的金色的眼睛。
金色的眼睛很罕见,是个吉兆。
并且,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孩子,大概率具备着魔法的才能。
人们对魔法并不陌生。身边某家商店的老板或许就会使用“让衣服更保暖”“让水果更饱满”这样实用但又不起眼的小小法术。
而像传闻故事里称颂的、被人们崇拜和敬畏的那些大法师就少之又少了,传说他们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知晓过去未来……人们对那些荒谬和夸张的想象乐此不疲。
有关魔法来源和使用的说道五花八门,但从没有过统一的定义。一些幸运儿或许会在某天突然学会什么法术,但这能力仿佛一种直觉和本能,就像动物也很难向人解释如何用四肢着地的方式高速奔跑。
那些才能出众的魔法师,更会收到富豪贵族们的招揽雇佣,得到钱财地位和种种好处,也就使得有关魔法的知识进一步被垄断。
即使如此,也有一点是作为常识被人们所普遍认同的:
“不论种族地域,每个孩子只有在降生在世上的第十二年,‘魔法的才能’才会在他身上开始展现。十二岁之前,无论在魔法上是天才还是庸人,都无从判别。”
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比如艾玛的父亲便对她的价值有一种聪明的认知:
他和艾玛的母亲都只是普通的人类,没有什么特殊的血统,那么艾玛才能的上限也是可以预计的——即使真有天赋,也绝不会太高。
因此他致力于在合适的时机将艾玛这笔生意做成价格合适的一锤子买卖,从未指望这个私生的污点能有什么光耀门楣的过人成就。
而到底要在她十二岁之前还是之后将她转手,这事让他苦恼了很久。
奴隶交易由来已久,懂行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门道。
十二岁之前谁都看不出魔法天赋的高低,即使卖家根据各种偏门的判别方式说得再信誓旦旦天花乱坠,十二岁后没能展现出才能,被投机失败的所有人怒而遗弃或低价转售之类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因此冲着魔法天赋来选拣奴隶的,越富有的买主越会从已满十二岁的孩子中挑选,依据其才能支付合适的价格。
而艾玛的父亲仍然唯恐她的才能只是一场空欢喜的假象,不敢等到她十二岁后,又担心她确有才能,太早放手而要低了价格。
那么他最终不得不被迫提早作出决断而省去烦恼的力气,或许也值得庆贺。
在艾玛八岁那年,她的父亲因为生意上的失败,在极度缺钱时以一个不那么让他满意的价格将她卖给了下一位投资人。
艾玛对此并没有太多感想。只是第一次,她对于母亲在前年因病离世这件事感到一些庆幸。
那之后艾玛的生活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换了个更大的房子做打扫的工作,换了个人计较她可能带来的利益。
年岁逐渐增长,她离十二岁越来越近,又在这时跟着买主跨过沙漠去行商。
而这之后发生的事也很好理解。这类生意之所以具有那样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它也有着与其相匹配的高昂风险。
沙漠强盗洗劫了他们的商队,杀光了具有反抗能力的人,而像艾玛这样的奴隶,和那些染血的赃物一起被当做商品送到城镇上的地下市场,置换物资与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