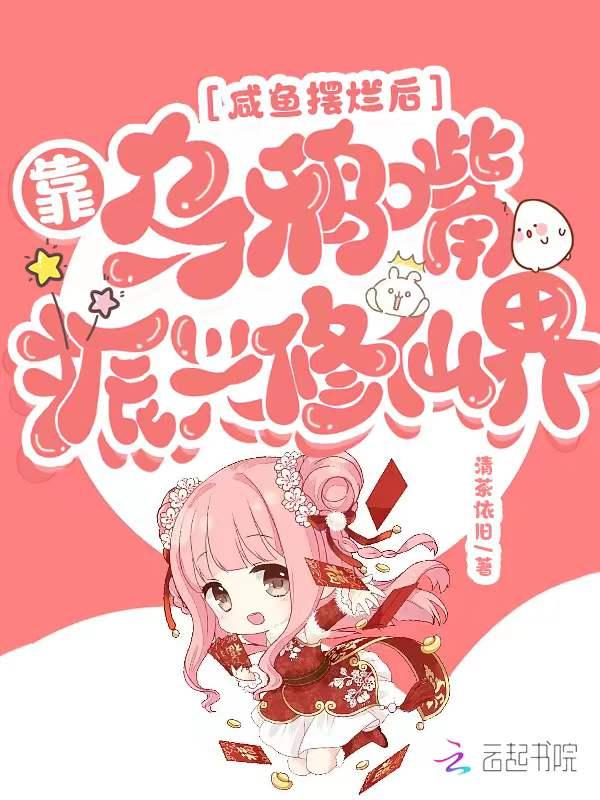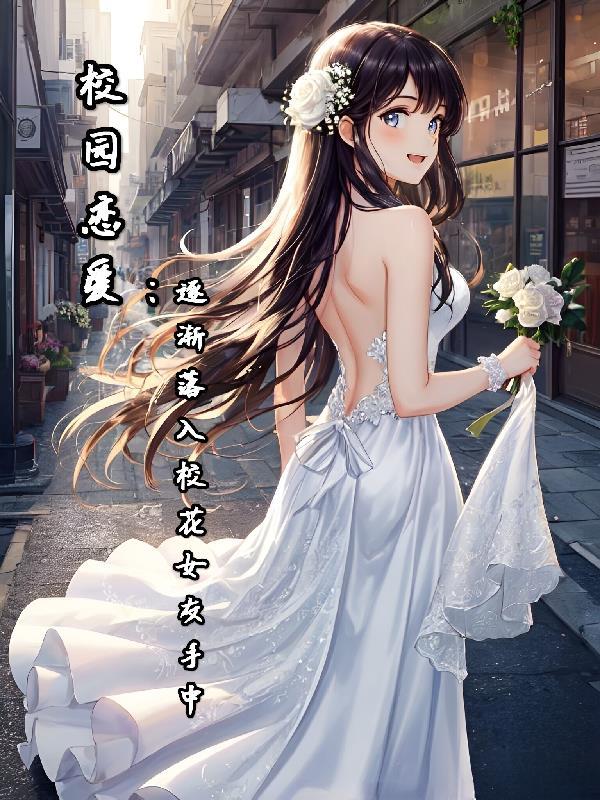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长乐怪谈 > 第 26章(第1页)
第 26章(第1页)
黏腻的帐中香燃到了尽头,红色帷幔下晃动的身形也停下了动作,只余满室静寂。
许久,一只莹润雪白的手腕颤颤巍巍地伸出来,拨开一条缝,逐渐露出一张汗涔涔的脸,那女人美极了,是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魅。
脚趾尖儿刚点地,一条粗黑手臂就伸了出来,一拉一扯,女人就如风中残柳,惊叫着,再次被拉进了帐中。
娱戏直到夜幕降临才真正画上句号。
餍足的男子半靠在榻上,吃着侍女送到唇边的甜橘,眼睛始终定在梳妆镜前的女子身上,从她葱根般的脖颈,到袅袅腰身,视线朝上,最终落在镜中那张脸上。
那是他从十四岁时就惦记上的脸。
每当午夜难眠时,他总会想起那个林子,那棵老树,那缠在一起的人。他和她最亲近的一次接触来得猝不及防,当时看到她落水,几乎是本能的,他立即就跳了下去。
其实,他水性很差,可那位骄矜的解元大人更差,所以是他抱得了美人。
那个简单的不能称之为拥抱的动作,却在此后数年让他回味无穷,即便身下躺着的不是她,可只要闭上眼,回想着当日指尖的触感,他就好似升了仙成了佛,拥有无尽的精力。
而今,他真的拥有了她。
抬了抬手,侍女立即躬身退了出去,他说:“过来。”
女子身形僵了僵,随即就放下梳子来到床边,从案几上掰了一块橘瓣,然后抬眼看他:“还吃吗?”
杨涵笑吟吟地把头凑过去,张口接了,只是还没反应过来,带着橘香的吻就落了下来。
女子气喘吁吁地退后两步,声音微哑但格外平静:“你说的,可还算说?”
杨涵满足地擦擦嘴:“自然算数,不就是个为你家的解元郎求个差事嘛,书院先生怎么样?”
“……当真?”
“哼,当真。”杨涵不屑地撇撇嘴,“你身上的伤是他打的吧?这种狗东西,你还跟着他做什么?”
说着,他长臂一揽,把人带到自己怀中,凑到耳边说:“娶你自然是不成了,姓邢的得罪的是蔡大珰,我可不敢老虎头上拔毛,只能委屈你做个外室,但你放心,荣华富贵不会差了你的,比你跟着那废物强一百倍,怎么样?”
李念如使劲挣了挣,却被抓得更紧,她吃痛一声:“我……我们之前说好的……”
当时为了把人哄到手,杨涵算是软硬兼施,最终总算用“威逼”把人吓住了。第一次的时候,李念如哭得太厉害,他就信口哄她:“跟我两年,腻了就放你走。”
两年……如今过去大半年,他可还没腻呢,不但没腻,还颇有些食髓知味的意思。
杨涵不耐烦地捏着她下巴:“我又没傻,记着呢,这不还没到两年呢,急什么?”
李念如终于挣脱了他的钳制,慌里慌张地退到一边,低着头讷讷道:“天晚了,我先走了。”
说罢,就不管不顾的快步离开了,就好像身后有人拿刀在追赶她似的。
杨涵烦躁的一脚把案几踢飞了出去,撞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把刚进门的管家吓了一跳。
杨涵抬起一只胳膊,脸上的戾气更盛,指着管家:“这火烧得还不够旺啊,去,再加把柴,我要让她彻底死心!”
南宫明白了李无忧的沉默,此刻,二人躺在房顶上,听杨涵在屋内叫嚷,说着无耻的混蛋话,只觉得一股浊气积在胸口。她一拳捶在了李无忧肩膀,后者被她打蒙了:“……干嘛打我?”
“烦。”南宫枕着双手,看着泼墨一般的天空,叹气。
李无忧比她更烦,但总不能还回去一拳,只能无奈苦笑:“那下次打我之前先说一声,我做个准备。”
南宫气哼哼地说:“李无忧,人间男子都这样吗?”
“哪样?”
“像邢解详那样,像杨涵那样……”南宫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觉得他们都很讨厌,也不是真的疼惜李念如。”
李无忧沉默了一瞬,才说:“人的情感是幽暗曲折的,邢夫子喜欢李念如,杨涵对她也有两分真心,可他们却都更爱自己。”
南宫听得云里雾里:“什么意思啊?”
李无忧笑了笑:“就说邢夫子,他听信流言,问也不问就动了手,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说白了,他真的体察过妻子的痛苦吗?”
李无忧也学着南宫的样子,枕着手臂,两人并肩躺着,“杨涵呢,色欲熏心占了多数,还有经年日久的求而不得作祟,心里有些扭曲,用伤害去表达爱,最终也只会让李念如惧怕他,却不可能爱上他。”
南宫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突然问:“李无忧,你有喜欢的人吗?或者,以前喜欢过的也行。”
“……以前没有。”李无忧眼眸微垂,视线从身边的人脸上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