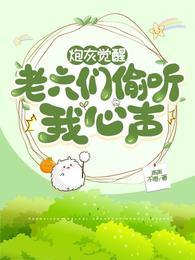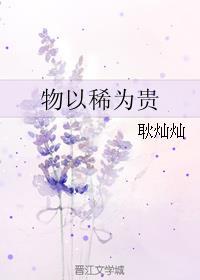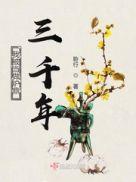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唐宫囚徒 > 后会无期(第2页)
后会无期(第2页)
更有言官道邠王在长安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有预知天象之神力,实乃怀有不臣之心。
但也有不少官员出面维护李守礼,言他大败突厥,平定北境之乱,又制止了一场宫乱,及时交出蜀军虎符。言那日私自用兵,乃太平公主拿章怀太子妃性命相威胁,百善孝为先,邠王之举,是被逼无奈,情有可原。
两边各不相让,一场朝会因邠王吵得不可开交。
姚崇道:“调兵一事暂且不论,但邠王预知风雨之力,老臣是亲眼所见。但凡邠王上朝时带伞,必降雨水。”姚崇掸了掸自己有些潮湿的衣襟道:“就如今日,明明艳阳高照,忽而天降大雨,众臣均雨沾衣襟,唯邠王一人衣着干爽,不知邠王如何解释?”
众臣看看自己打湿的衣物,又看着殿上唯有邠王和陛下衣着清洁,不禁窃窃私语,难道邠王真有预知天象之能?这可是真龙之兆啊!
众臣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愈发玄乎,而李隆基始终不发一言,未出面制止。
李守礼看了李隆基一眼,面色如水。耳边仿佛还响着李隆基稚嫩的声音:“二哥,你疼吗?我给你吹吹。”
李守礼忽然走至殿中,将笄板扔于地上,除下外袍。繁复的亲王朝服被一层层解开,直到李守礼脱下中衣,露出满身触目惊心的伤痕。
除了殿中众臣惊地一声声的吸气声外,还回响着李守礼清冷悠长的声音。
他俯身向殿上的李隆基拜下:“启禀陛下,臣自幼在宫中代父王受过,落得满身伤痕。能预知风雨,并非天赋异禀,而是每逢阴雨,伤处便会隐隐作痛,因而得以提前预知。谣言止于智者,还忘陛下严惩造谣之人,还得日月清明。”
邠王以亲王之尊,当众裸露伤痕,坦言儿时之过,无异于将自己的颜面放于地上任人踩踏,这种折辱之姿,就连向来古板的姚崇都看不下去了,不再言说邠王之过。
李隆基走下大殿,亲自拾起外袍为李守礼披上,将他扶起,冷声对着百官道:“调兵一事,朕事先已应允,无论何人再纠着此事不放,恶意攻讦邠王,离间朕与皇兄之情,朕必严惩不怠!”
李隆基已盖棺定论,邠王今日又姿态十足,吵闹了一上午的朝堂,总算安静了下来。
“报!益州军报,西南大捷!”一个传信兵捧着军报直入大殿。
李隆基脸色一喜,拿过军报逐字浏览,看完后,不禁龙颜大悦。他看完后,将军报递给兵部尚书姚崇。
益州来报,趁武周至睿宗内乱之时,吐蕃趁机吞下安戎城、维州,切断了大唐与西域联系的西山道。致使川西走廊中断二十余年,使大唐丧失了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商队中断,不仅影响大唐国库盈收,更给西南门户带来隐患。
近日,剑南道一个不知名的小将联合当地羌族部落,突袭安戎城,不仅重新夺回安戎城,让川西走廊重回唐军控制,还趁机拿下了松州、巂州,切断了吐蕃与南诏的联络线,至此,吐蕃东进通道被阻断。
“张守珪?何许人也,老夫怎么从未听说过?得如此将才,实乃大唐之幸啊!”姚崇捧着重若千钧的捷报,心中除了纳闷,还有感慨,先是平定北境,再是西南大捷。天命依然站在大唐一边啊。
李隆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这个张守珪,别人不知,他却对他的来历一清二楚。他指着李守礼笑道:“这张守珪的来历,还是让邠王为大家说说吧!”
邠王,这张守珪与邠王有何干系?
李守礼看着众官好奇的眼神,悠然道:“张守珪,乃故中书令张柬之收养的义孙,现承继襄阳张氏一门香火。”
张守珪众人未曾听闻,可这德配宗庙的张柬之,无人不晓啊,邠王娶的不正是张相唯一的孙女张氏么?这么说来,张守珪乃是邠王妃的义兄。这就难怪了,张柬之亲自教导出来的嗣孙,能取得西南大捷也不奇怪。
刚才还在攻讦李守礼的一些官员,目前有些慌乱,这张守珪立下了不世之功,又如此年轻,日后必得陛下重用,与邠王还是姻亲。。。。。。
李隆基饶有趣味地看着李守礼,又一次,他生生地将一局死棋逆转乾坤,偏又让人挑不出任何错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罢了,这样的人,还是莫要当作对手。
李隆基让众人散朝,唯留下李守礼单独叙话。
太极殿,香烟袅袅,李隆基与李守礼一同看着大唐江山舆图,就像一年前,他二人在相州太行山上,注视着大唐广阔的山水。
“二哥这次真的要抛下我不管了。”
“我早就说过,帝王之路,只能你自己走。”
丹凤门前,那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就如耸立于天地间的山峰,岿然不动,永远微笑地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