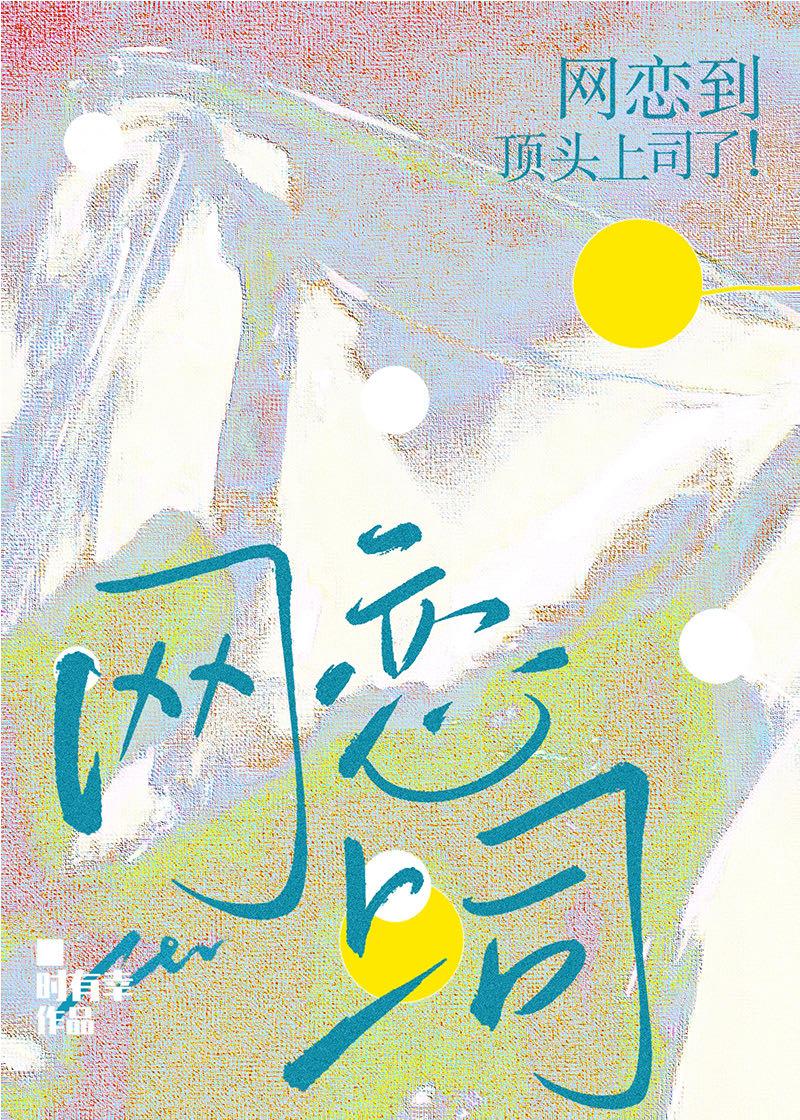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风前絮 > 金榜榜眼之殇(第1页)
金榜榜眼之殇(第1页)
时至酉时,陶府中人已全然知晓陶然高中榜眼之事,虽不甚欣喜,但庆幸终是进士及第,此后也算彻底脱了商籍的帽子,改了陶家的命。今后,门楣光大,顶天立地,夫妻二人面上自是不再同小市民之流。
众人从外至内阵仗摆好,就是不见陶然回来。菜已凉了,小厮跑进来,陶父问道:“人呢?”
那小厮摇摇头。
陶父跺足点拐杖急道:“再派人去找呐!”
原来陶然不在别处,却是找何督喝酒去了。他从来克己,往日除非官家礼节,否则滴酒不沾,今日却主动喝得醉醺醺的,面颊绯红,抻手倒在桌面上。
何督见状一笑,语辞囫囵道:“怎。。。怎么了,榜眼还委屈你了?”
陶然伏面,闷声闷气地答:“你不懂。”
“我?”何督醉醺醺地指着自己,哂笑道:“我怎么不懂?我以前,就是个。。。就是个同进士出身。”
他伸出小拇指,眯眼道:“差。。。就差那么一名,就名落孙山了。”
陶然闻言也抬面而笑。
“我要能进士及第,得高兴死,比范进还疯!怎么了。。。。怎么了?我差一点儿名落孙山,现在还是个京官儿不是?”
陶然笑着摆摆手,要把自己撑起来走回去,几次却都失败了。
“哎,”何督感慨道,“你还年轻,到我这个年纪,就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娶个媳妇。”
陶然笑笑,又试图把自己撑起来。
“你还记得。。。还记得。。。季府的二姑娘吗?”
“嗯?什么?”
何督笑着指指自己:“我以前,可喜欢她了。”
陶然脑袋懵懵的,却问:“你喜欢她?”
“当然了,”何督起身,打了个嗝,“可是人家,看不上我。。。。。。看不上又怎么?你看,现在也一把火没了。”
他说着说着,像是有些委屈起来。
陶然摇摇食指道:“你不厚道,这话像是报复解气似的。”
“我有什么气可解啊,人家活着,死了,都看不上我,我告诉你,陶然,我。。。我没那么小气。”
陶然笑着出气,摇摇头,含糊道:“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何督不觉,仍在劝道:“你啊,把。。。把自个儿放平,听见没!别总。。。撅着个读书人的臭脾气,这官场上的事儿,一把火烧了的有,一把火起势的也有,好事还在。。。还在后头呢。。。。。。”
陶然终于跨出房门,笑着坐在门槛上流眼泪,半晌后,又爬熊似的伏膝在地爬了两步,才终于站起来走了回去。
陶府仍旧灯火通明,红绸满院,但却一个人也没有了。父母得知陶然在何督处喝得烂醉却不肯回家,气得去睡了,喝令全府上下不得有人照看于他。
到了府内,他不小心撞到桌边,靠着桌腿小憩了一会儿,又踉踉跄跄地往偏院走。静堂在房中答写今年殿试的考题,越写越气,这字字句句分明与季府之变、京城之势严丝合缝地相对,她言辞激烈,写到最后几乎是猛地一丢笔,墨汁重重地溅洒在绢制灯笼上。
她想到季府的火光,父母的惨死,陶母打翻了牌位,正兀自平复着情绪,不想外面传来一声闷闷的响,然后是阵阵呜咽。
静堂几乎从不出这偏院,她想了想,起身出去,见陶然靠坐在月亮门外,嘴里不知含糊地在说些什么。

![我貌美娇弱但碾压副本很合理吧[无限流]](/img/806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