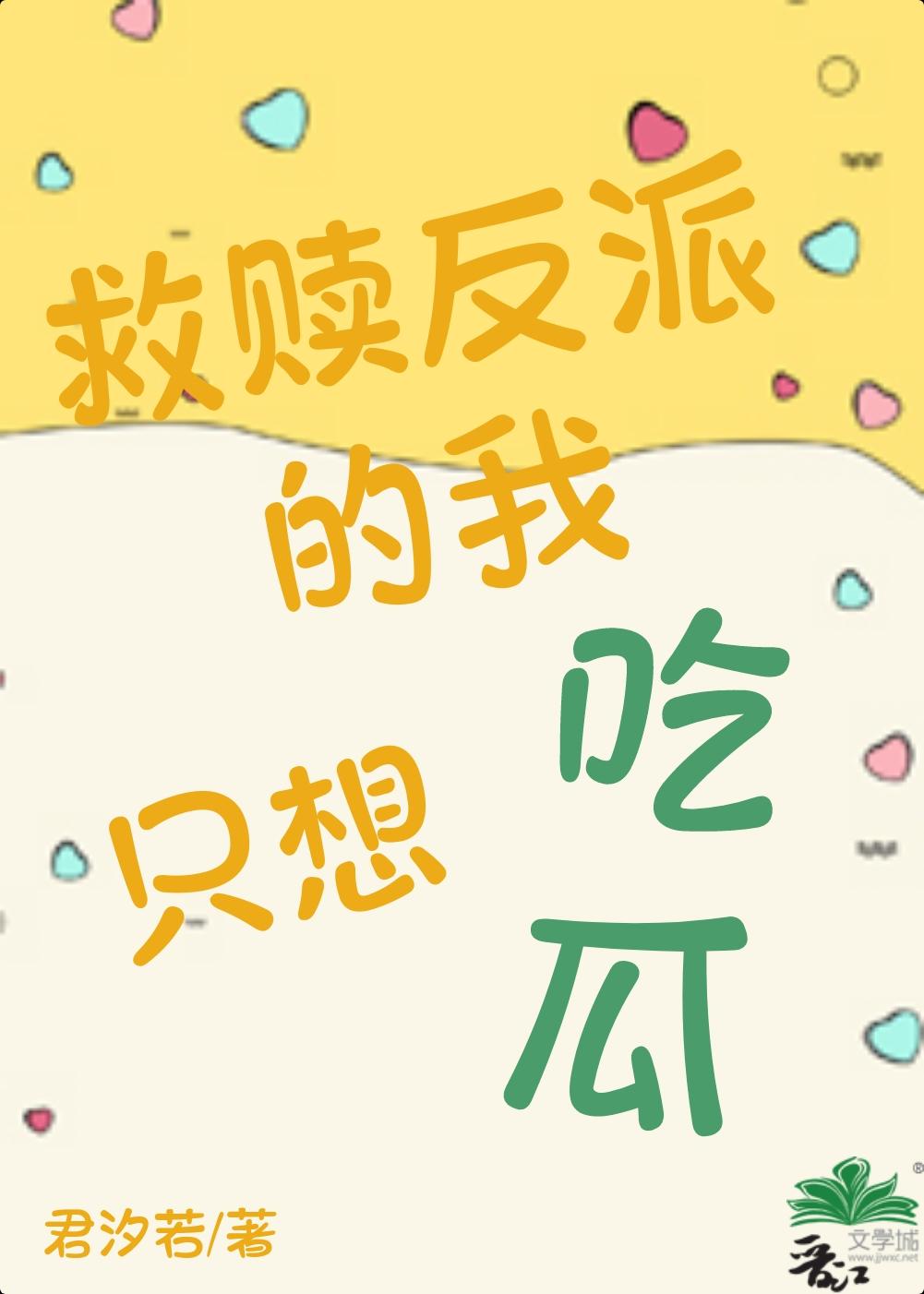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观云三百年 > 第156章 三百年故梦双骄(第2页)
第156章 三百年故梦双骄(第2页)
司徒悯灯不如他身高体壮,每次却也能将人稳稳的带回空荡荡的东方府。
有一回东方情白想起到一个事情,问道:“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你那时候是怎么办?”
他指的是山匪打着起义名号杀烧抢掠,灭司徒满门一事。
司徒悯灯说:“还小,记不清。”
到底如何会记不清呢?那些刀枪与血肉,哭喊与挣扎,在幼小的时候就根植入司徒悯灯的骨头里,他忘也忘不掉的随着母亲忐忑一路来到王都投奔姑姑家,没到目的地母亲便亡故了,自此司徒悯灯在这世上血亲只余下了姑姑,还有这个壮硕到吓人的表弟。
第一次见面,誓要立威的司徒悯灯提剑给了那追野人的小孩一个血呲花脸,他原不识得那是谁,只知道进了王都,也不能让人欺负了。然那孩子皮糙肉厚,满脸是血也不见得掉一颗眼泪,执着的追野人一下就跑走了,东方府的仆人大惊失色的跟在身后吃力的跑,喊着“世子世子”时,司徒悯灯才晓得自己伤了姑姑的儿子。
他心怀愧疚,想给“阿宝”道个歉,没等张口说出,阿宝就朝他扑了过来,拳头虎虎生风,俩人压在地里打了十几圈,他们头顶是高悬的日,一丝不苟地照耀着年幼的两个小身体。
东方情白问他当初是怎么过来的,司徒悯灯其实想说:“多亏你小子,日日找我打架。”
然而同样的法子在他身上是没有用了,东方情白萎靡不振,只晓得浑浑噩噩的跟在他身后转,一入夜就哭,不是缠着他去陵墓,就是穿盔戴甲的骑马出门,说要去边疆,把坑害了东方家族的保部氏灭国。
除夕的这日夜,他又要出发了。
司徒悯灯终于是忍无可忍一巴掌呼他后脑勺:“发什么疯癫痴症!滚回去睡觉!”
少年东方情白亮闪闪的眼睛一下就暗淡下去:“你怎么打我?”
“我早该打你了。”司徒悯灯扯过他的马绳在腕上缠住好几圈,“下来!”
“不下!”十三岁的东方情白吼道,“我自己去!妈的,我再不要跟住你,再不要问你,再不要和你说了!”
东方情白拔刀割断缰绳,驱马跨出仆人跪拦的几十人,一下子冲出东方府,夜色沉沉,银色的雪盔在月下反回盈盈微光。
“阿宝!”
司徒悯灯高喊一声,弃下断缰,即刻寻马追人。
彼时司徒悯灯刚凝出丹元一颗,剔透如琉璃,他没有拜师,因此运用的不自如,寻得东方情白用了足足一个时辰。
在王都边城的一座山脚下,彼时东方情白牵着马正要上山过境。
时值寒冬,大雪封路。
司徒悯灯默默跟着他艰难的上到半山腰,终于开口:“回家,阿宝。”
东方情白至此转身,眼泪在脸上凝成冰,嘶吼道:“你别叫我阿宝!”
吼声回响,山峦顿时如震。
“回家,东方情白。”司徒悯灯从善如流,“姑姑不会希望看见你这样,要杀敌复仇,也等再长大一些,等我们都大一些了再去,不好吗?”
“他们说你要上山修道了。”东方情白委屈巴巴地吼,“狗屁相依为命!都是骗我的!现在说等长大一些也是骗我的!你要修了道上天去,留我一个人在地上!你早是这样打算的!”
司徒悯灯看向四周皑皑白雪,轻声道:“东方情白你别吼。”
“那你上山修道吗?”东方情白吸了吸鼻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