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广夏:文德皇后 > 蛛网(第2页)
蛛网(第2页)
“母亲说,祖母今年气疾比往年更难捱……”李承宗认真地回想,“我初时不觉得,但我回长安这几日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医官进出国公府。”
“我听说,我母亲连同另外四位姨母均在不同寺庙为外祖母造像祈福。”柴令武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认真地求得长孙青璟的认同,“舅母,我母亲和姨母们共造了五座佛像,不可谓不虔诚,神佛一定会保佑外祖母痊愈的,是吧?”
孩子们一时伤感起来,在他们的认知中,造像总是和一些不吉利的事情关联着。
“父亲说,我们家上一次造像还是二叔九岁时,他一年里染上两次疫病,奄奄一息……”李承宗的话惹得另外两个孩子倒抽一口冷气,长孙纫佩的一双杏眼中甚至蓄满了泪水,误以为今早还与自己谈笑的舅父快要死去了。
长孙青璟也后怕似的颤抖了一下。“那后来呢?”她明知道丈夫有惊无险,却还是忍不住问道。
“母亲说,上天还是不忍心带叔父走,有佛护佑,这病就突然转好了。”李承宗突然似懂非懂地问道,“婶母,那我祖母有五座造像,比叔父当年还多三座,她应该也会转危为安吧?”
“会的,一定会的!”长孙青璟无意再追问细节,只是把三个孩子聚在一处安抚着,“今日我就问到此处,猞猁归你们了。你们无需胡思乱想,祖母一定无甚大碍。你们度过腊月,看过大傩,准备过元正节就是了。去,把大氅穿好,不要受风寒!”
长孙青璟指着匆匆跑来为小郎君与小娘子们添衣的婢女说道。
她不再询问窦氏病情,以免在李家的婢女面前呈现还未成礼便多管闲事的形象。
长孙纫佩捧着鸟笼,有些担心地贴近长孙青璟:“阿姊——嗯——舅母,你还没问我呢?”
她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就被收回了罗浮凤的使用权。
长孙青璟笑着捏了捏她藕粉色的面颊,把精致的鸟笼与罗浮凤一同掖进她怀中:“你光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就喜欢的很。舅母不舍得考问你,罗浮凤归你了。”
她不想再问,不忍再问,尤其是套问一个天真无邪的、全身心信赖自己的孩童的话。
接着的半日里,承诺去去就回的独孤璀便再也不见踪影。三娘与四娘从婢女处得知长孙青璟一人无所事事,四处闲逛时,便叫上她一同下双陆棋。
长孙青璟的棋艺与婚礼那天一样糟糕,只可惜没人替她饮罚酒。
李琼曦笑道:“胜之不武。今日我小赢一局。我猜二郎知道了肯定不服,定要为你出头,从我这里扳回一局。”
李陇月埋汰道:“我就时常弄不明白你与二郎二人平日里争什么高下?三胡与毗提诃争骑射,智云与大德争弈棋,我都能懂他们争来争去的深意,无非要父母多一点夸赞,亲朋多一些提携。你一个已出嫁的阿姊,处处喜欢压过弟弟一头,却是为何?难道还能封为柱国,拜为卿相不成?”
“四妹说得也未可知呢!”李琼曦自嘲道。
长孙青璟方才刚听得独孤璀讲述三娘与二郎姐弟间趣事。说是三娘未出阁前,常假扮男子带着二郎出游,逼着二郎称呼自己兄长,否则便不带其出行。
三娘出阁之日,其余亲眷下婿之时均是将竹杖高高扬起,点到为止,偏二郎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将新郎柴绍打出了一点不轻不重的皮肉伤,从而成为柴、李两家的笑谈。
可见姐弟二人一脉同气。对于四娘的调侃,长孙青璟自然一笑置之。
三人正在点筹之时,行障外婢女犹犹豫豫这不敢近前,李陇月起身,二人在行障处低语了数句。
四娘回到案前道:“我以为是什么要紧的大事,谁料又是纫佩不让人省心,说是跟表哥们口角气哭了,大吵大闹,两个表哥低头赔罪都不好使。我这就去哄哄她——三娘你陪着妹妹多聊一会儿。你不准再灌她酒,她明日还有庙见这一桩要事。”
“你放心,我们接着玩投壶。青璟肯定不输我——你也不想想她父亲的射术何等了得?谁赢了灌死谁还说不定呢?四娘,你怎么老觉得我会欺负她?——还有,记得替我扇令武这小子两巴掌,告诉他下次再敢惹事欺负妹妹,他阿娘将他倒挂在房梁上抽耳刮子!”
“你这当娘的,说话也真是不成体统!”四娘揶揄着离去。急促的脚步却与解决孩童间纠纷的意图殊为不符。
长孙青璟与李陇月热络又疏离地度过了半日,热络是因为长孙青璟确实是李陇月最亲近的弟弟的妻子,爱屋及乌,便对这个纤弱倔强的娘子多了几分好感。
两人聊社交、聊骑射、聊饮食,聊服饰,无所不包;疏离是因为两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些会引来对方伤感忧虑的话题,比如高夫人为继子所逐,比如高士廉贬官朱鸢,比如李渊常年被皇帝猜忌起用,周而复始,如履薄冰的经历。
比如窦夫人那哑谜一样在无甚大碍与造像祈福之间游走的病症。
一张谎言编织的巨大的温柔的蛛网在长孙青璟的头顶徐徐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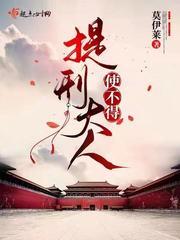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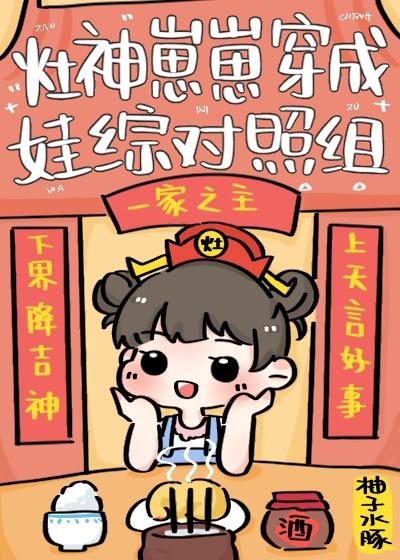
![狗血文女主摆烂了[快穿]](/img/158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