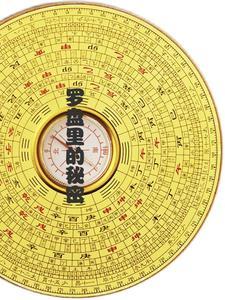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诗吟刀啸 > 7080(第11页)
7080(第11页)
两人谈话期间,谢缘觉还在欣赏丰山胜景,她身为长安人氏,活了二十年,人生第一次来到长安最有名的踏青胜地,对于此处的美景自然是怎么也看不够,便没有注意到另一边颜如舜与尹若游究竟说了些什么。待她追了会儿蝴蝶,闻了会儿花香,听了会儿鸟鸣,又坐在清溪边玩了会儿溪水,这才抬首一瞧,见凌岁寒依然独立溪边,低头看着溪中倒影,竟像个雕塑般一动不动,她的心弦却倏地动了一下,不由得思考起,之前因为诸事烦扰让她一直没来得及思考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最近几日凌岁寒总是对自己十分关心?
而细细思索,凌岁寒的突然转变,似乎还是在那天夜里她们吵过架之后。
那天夜里,她们除了吵架,到底还发生何事?谢缘觉不放过那晚的所有细节,苦思冥想半晌,一个念头霍地钻进她的脑袋里,她怔怔凝望凌岁寒许久,直到一阵大风夹着几片绿叶吹来,吹得凌岁寒的素白衣角登时在她眼前扬起,她的心却在这阵大风里沉下去。
——自己怎么忘了,凌岁寒还在服丧期间,那么她父亲或母亲应该去世还不到三年,如何可能是……
虽这样想着,谢缘觉仍不愿放弃任何一点微弱的希望,向她唤了一声:“凌岁寒。”
这个名字,这个在她家破人亡之后的新名字,在今日此刻传入白衣刀客之耳,犹如一支利箭刺中她的心口,脑海中父母的幻影如烟雾消失,让她不得不从多年前的回忆中抽离,愣了愣,道:“什么事?”
谢缘觉斟酌语句,不知从何开口,毕竟她不能直接询问,倘若对方与符离毫无关系,她要如何解释凌澄是谁?又要如何解释她怎会和“谋逆罪臣”的女儿相识?没奈何,她只能小心试探,在纠结间突然灵光一闪,起身走到凌岁寒面前,压低声音:“我听说,昨日你在润王府,劫持了润王谢惟的女儿?他的女儿应该不止一个,你劫持的那位叫什么名字?”
自从隐约猜到谢缘觉的真实身份,凌岁寒如今在她面前比从前更为谨慎,摇首道:“我怎么可能知道亲王女儿的闺名?不过我听尹若游称呼她为永宁郡主。”
“永宁郡主?”谢缘觉纳闷道,“润王并非太子,他的女儿怎么会是郡主呢?”
“我又不是朝廷中人,我哪儿知道?”其实凌岁寒对此亦颇为好奇,“要不你问问尹若游,或许她会清楚。”
第76章凌霄宝剑侠士风,诽语谗言小人心(二)
第一次试探失败,谢缘觉又看了凌岁寒一会儿,才转过身,走向尹若游身边,询问这位“永宁郡主”究竟是何来历。
“你问谢丽徽?”
“谢丽徽?”其实谢缘觉的堂姐妹太多,她幼时又几乎不出睿王府,只有偶尔在她身体能坚持得住的情况之下参加过几次宴会,在宴上与别的宗室贵女有过几面之缘而已,她之所以对谢丽徽的印象深刻,还是因为她的这位堂妹与符离的关系不甚友好,符离曾在她面前说了许多关于谢丽徽的坏话,她依稀记得她的这位堂妹小字阿鹦,原本的封号似乎是什么宝阳县主?
“她什么时候成了郡主?”
尹若游道:“你怎么知道她从前不是郡主?”
谢缘觉道:“崇制,天子之女为公主,太子之女为郡主,亲王之女为县主。润王如今还不是太子吧?”
因此昨日听尹若游在谈话中提起“永宁郡主”这四个字,她已觉得蹊跷,但当时她更好奇尹若游的事,便未打断对方的话。
“天子一言九鼎。”尹若游笑道,“只要当今皇帝愿意,莫说亲王之女,哪怕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他也能找到一个由头封郡主的。”
“照这么说,是圣人很宠爱谢丽徽了?”
若他只是单单宠爱谢丽徽这一个孙女也就罢了,谢缘觉怕的乃另一种可能:圣人有意册封为润王谢惟为太子,可谢惟非嫡非长,料想朝臣必定反对,圣人便暂时将此事搁置,却给予谢惟太子般的待遇,譬如册封其女为郡主。
谢缘觉只在乎名,既不爱权亦不爱利,什么公主郡主县主的差别她并不在意。待圣人百年之后,该由谁来继承大统,她原本也不关心,但凌禀忠生前与润王颇为不和,倘若润王继位,他绝不可能为凌禀忠平反,符离如果还活着,就得一辈子背负着叛臣之女的罪名东躲西藏——就冲着这一点,谢缘觉也希望是自己的父亲承袭帝位。
尽管之前尹若游说过,当初凌禀忠被诬谋反下狱,睿王始终袖手旁观,不理不问,她也承认自己的父亲为人处事谨小慎微,但当了皇帝那就自然不同,到时候父亲不需要再畏惧任何人,他想要为谁平反,岂不是他一句话的事?
“看来你们也都赏够了风景,我们边走边说吧。”尹若游继续在前带路,途中低声为她们解释,“当年润王子凭母贵,在天子跟前很是受宠,然则自从吴贵妃去世,圣人对他愈发冷淡,而睿王比他年长,比如今谢崇皇室还活着的任何一位皇子都要年长,又胆小如鼠,这些年来办事都没出过岔子,在朝中素有忠孝之名,因此朝中立睿王为太子的呼声很高。本来润王还有尚知仁当他的盟友,可近年来尚知仁已不再是圣人最宠信的臣子——”
“现如今皇帝最宠信的臣子是谁?”凌岁寒插话问道。
“文臣是御史大夫贺延德,武将是霍阳、河东、平宣三镇节度使魏恭恩。”尹若游对朝堂局势的了解,令凌岁寒和谢缘觉都自叹弗如,“尤其是魏恭恩,也不知他到底给当今天子灌了什么迷魂药,他经营河北一带多年,麾下精兵无数,权势不下当年的四镇节度使凌禀忠,而圣人明明是多疑善忌的性子,却对他极为信任,毫不猜疑。因此在润王看来,倘若他与魏恭恩结盟,他有了魏恭恩的支持,会更容易登上大宝,但这也造成了他与尚知仁的分歧。”
“分歧?”谢缘觉狐疑道,“尚知仁并不希望润王与魏恭恩结盟吗?”
“这还用说吗?”凌岁寒冷哼一声道,“尚知仁当了十几年的宰相,把持朝政多年,如今天子又有了新宠臣,分走他的权力,他已不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怎么能够容忍?若他没有排除异己之意,那也就不是他了。”
尹若游微微摇首:“其实最初魏恭恩能得到圣人重用,也有尚知仁的举荐。直到后来魏恭恩势力坐大,尚知仁渐渐对魏恭恩有所防备,如你所说,确有排除异己之意。但他从前偶尔与我聊起魏恭恩此人,我听他话里的意思,他也是真的怀疑魏恭恩有谋逆叛乱之心,是以对此颇为忧虑。润王则认为他是杞人忧天,一心一意要拉拢讨好魏恭恩。”
当年凌岁寒的父亲便是被诬造反而死,因此缘故,本来凌岁寒最是厌恶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之下随随便便冤枉一个好人,然而听罢尹若游这番话,她并未开口反驳,还是因为八年多前,她偶遇父亲的旧部李定烽,在李定烽的府邸住了两日,对方和她谈起朝局,言语中提及魏恭恩,也是一样的忧虑重重。
她自然是完全信任李将军的判断。
尹若游继续道:“所以,当初圣人在宫宴上给润王之女谢丽徽和魏恭恩之子魏赫赐婚,润王喜不自胜,尚知仁却大为恼怒。”
颜如舜恍然道:“难怪你和谢璋说,那两个杀手乃是尚知仁派来刺杀永宁郡主的,谢璋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你。”
果然,人与人之间得先有了嫌隙,离间计才能奏效。
“你说什么?”凌岁寒闻言一怔,显然更加在意尹若游话里的另一个关键,“谢丽徽和魏恭恩的儿子已成婚了吗?”
“你们不是问我,谢丽徽身为亲王之女,为何会是郡主吗?”尹若游道,“正是在那次宫宴上,不知因何缘故圣人竟突然想到给他们二人赐婚,同时册封谢丽徽为‘永宁郡主’。但目前他们只是定下了亲,只待来年完婚。”
“来年……这么早?”在凌岁寒的印象里,谢丽徽的年纪似乎比舍伽还要小个两岁?饶是她和谢丽徽的关系一向不大友好,她心底也不免对她生出一点同情,“她不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