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桃夭定终身-高冷帝君漫漫追妻录 > 攻纪(第1页)
攻纪(第1页)
冬月末,同约郑君子仪在滑地相见。同带了三千精兵,这是他做鲁君后第一次和其他国君会盟。秋天时他收到了纪国的求救信,父王的妃子纪氏也找到他,求他在齐纪大事上多想想办法。
当年父王在时,多次和齐国会盟也只是延缓了齐国攻纪之势。在同眼中,齐国绝不会放弃攻纪的打算,凭他和齐王诸儿的几次交手,他能感到齐王的野心和能力。
若他直接去求齐王,他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若他去求了母亲,母亲转头去求了齐王,这更是他无法容忍的,他不愿把母亲推到两难之境。
但他又无法直接拒了纪国,这样父王之前努力多年在诸侯间争取的影响力又要慢慢衰退了。
最后他硬着头皮给郑君子仪写了信。子仪倒是没有拒绝,只是转头忙不迭去了探齐国的心意,结果诸儿除了感谢子仪外,对郑鲁结盟完全没有意见,甚至在信中写道:"若一日得见郑鲁携手,共克时艰,未尝不是佳话一段。"
子仪完全糊涂了,齐国对纪国的态度是毫无置疑,可是齐国对鲁国的态度却让人揣摩不透,坊间传闻齐王曾秘恋当今鲁君同的母亲多年,如今同的母亲并不在鲁国,而是被齐王金屋藏娇。所以对于鲁国的邀约,子仪并没有贸然拒绝。
临近年底的冬日已经是十分冰冷了。同来到滑地时,滑地刚刚下过雪,天气放了晴,冰雪消融时人就愈加感到寒冷。
同本来比约定时间早来了一日,待等到第二日,郑君依然杳无踪影,却有郑国的使者带来了一封信,信上写郑国国内出现了内乱,国君需要先平内乱,安抚局面,抱歉不能赴约,待明年有空,再亲自邀约谢罪。
子仪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过是听说齐国在年底前给所有临淄的战士都发了往年双倍的俸禄,临淄城都在风传明年要有大战,因而今年年底才额外犒劳一线士兵。子仪既不愿再牵扯进这齐纪恩怨,亦不愿得罪鲁国,最后只得使出这个"拖"字诀。待到齐纪开战分出胜负后,郑国再选择站队不迟。
过了年,春天很快便来了。二月里,婉打算回趟鲁国,她离开鲁国已有大半年时光,心中念着子同和子友,归乡的心就变得无比急切。诸儿心中不愿,但实在找不出理由阻拦,一路送婉到了祝丘,眼见再往西便是鲁国费县这才停了下来,密密叮嘱了归期,才依依不舍地返程。
然而还未回到临淄,便有消息传来,周天子派人慰问纪国,因为纪国的大伯姬没了。
说来话长,这大伯姬按辈分算是当今鲁君的姑母,是息姑的亲妹妹,在息姑当政时嫁到纪国做元妃,当时还被周天子亲封为侯爵夫人。
后来纪君去世,息姑也去世,虽然伯姬身份尊贵,但纪国和鲁国早换了几重天,当今纪君虽然对她尊崇有加,但是在拉拢和鲁国关系时,依仗更多的是自己的妹妹,嫁到鲁国的纪氏,而非大伯姬。
如今大伯姬去世,天子突然派人前去慰问,大家不知道是天恩浩荡还是另有他图。毕竟纪国也是有女子嫁到天朝做王妃的,如今齐国对纪国虎视眈眈,天子虽然力有不逮,无法亲援纪国,但在此刻派人慰问逝者,未尝不是向诸侯表达自己的态度。而诸侯间群龙无首,有时一点微妙的态度,或许就能扭转或改变诸侯站队的风向。
子同听到这个消息时,只觉得头痛。大伯姬是鲁国女子,或许现在诸侯都等着看鲁国的好戏,表现的太亲密无疑于和齐国分庭抗礼,表现的太冷漠又容易遭人耻笑。最后,朝臣议论再三,决定比照周天子降低一级礼贽,派了申繻前去纪国慰问。这样在礼节上也算过得去。
诸儿却对这个消息莫名有些兴奋。他正准备攻纪,虽然打着齐纪九世之仇的名头,但纪国国土辽阔,若拿下纪国,眼红的恐怕不止是一两家诸侯;或许,可以拿大伯姬的死做一做文章,探一探他国的立场。
四月里,郑国、陈国收到了齐王的信,相邀在垂地会盟。子仪继位,全仰仗齐国之力。如今大战一触即发,子仪早等待着齐国的号令,所以收到齐国来信第二日,他便率了几千精兵直奔垂地。
陈国和齐国在战场上虽不似郑齐互为臂膀,但也没有断了往来,这些年一直有陈国女子嫁到齐宫,前有陈国公主做了老齐王的妃子,后来陈国又要把新的女子嫁给诸儿,诸儿一味推脱,最后由彭生娶了那女子。陈国和郑国更是一向交好,郑国国君子仪的母亲本是是陈国人,子仪当时避难也曾得蒙陈君收留。
五月的垂地已经有初夏的热了。这次会盟十分仓促,因诸儿是在回临淄的途中向郑国和齐国发出邀约,他调转原本回临淄的部队,直奔离郑国不远的垂地。
三国国君会面直奔主题,齐国已动员三军,会以全军之力攻打纪国,届时郑国和陈国无需大军支援,但望稍稍出兵从形势上给纪国造成压力。子仪和陈君听了连连同意,既能表明和齐国在一起的立场,又不用大规模折损兵力,这正是两国求之不得的。
三日后,诸儿从垂地出发,直接朝纪国边境进发。公孙止在临淄接到通知时心中忐忑不安,他本想劝诸儿回临淄休息调整后再发动战争,但是诸儿打仗素来有自己的一套法子,每次的作战计划从来都是天马行空,少有人能猜透他的想法。
五月的临淄城,上半月还是尘土飞扬、人声鼎沸、马声长鸣,到了下半个月似乎一下子城就空了,一批一批的军队从临淄出发。
城里有些年长的老者说活着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士兵。
燕将军已近古稀,仍然被诸儿任命为上军主帅,连城作为副帅;诸儿自任中军主帅,公孙无知为副帅;公孙止为下军主帅,小白为副帅。
齐国的老中青能干之辈,几乎倾巢出动。公孙止和燕将军同时从临淄出发,公孙止疑窦重重,忍不住问燕将军:"老将军,咱们大王往常作战往往是轻装简阵,善偷袭、善攻心、善以少胜多。当年哪怕攻打戎狄,千里作战,不过才万余士兵。为何这次要几乎发动我整个大齐兵力?以我看,纪国的实力并不值得咱们如此兴师动众。"
燕将军脸色黝黑,皮肤似树皮一样虬结,只有那双眼睛中的坚毅,偶尔会泄露出他曾陪伴了两任君王,经历了大小逾百场战争的秘密。
他早年跟从夷仲年,从一名饲马官到变成夷仲年的贴身侍卫,再一步步被提拔,直到成为职位仅次于夷仲年的将军。诸儿自幼和夷仲年情同父子,夷仲年死后,诸儿就本能的亲近燕将军,两人的关系更是在无数的刀光剑影中变得默契异于常人。
他犹记得两年前诸儿要增兵扩军时,曾问他:"燕将军,我这算不算穷兵黩武?这仗一旦打起来,恐怕又有无数人要颠沛流离了,这会是我大齐百姓想看到的吗?"
他当时的回答是:"如今鲁国、郑国国君皆羸弱,卫国国内局势亦是扑朔迷离,而大王却如日中天。往坏处想,是我齐国失去了左膀右臂,但往好处想,这正是趁势扩张的绝佳时机。大王这个时候扩军,臣认为再合适不过。"
"纪国这几年虽一面四处寻人和我齐国求和,另一面又偷偷大扩军备,若要彻底征服纪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于这场战争。他日若在九泉之下见到父王和夷将军,你说他们会赞同还是责骂我?"
"若此战能换来齐国未来数十年的稳定,更丰盛的资源,更多的人口,那么百姓定然明白大王的苦心经营。"
"纪国之战,他们必倾尽举国之力来对抗,以前的法子,偷袭多获些兵马粮草,围城让对方不战而屈,恐怕在这场硬仗里都用不上。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兵力形成碾压之势,让纪国人从上到下,从身体到心理上屈从我们。"
。。。
"燕将军,我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军密?若将军为难,不必回答。"公孙止的话把燕将军从思绪中拉回。
"公孙大人,纪国百年前和我齐国同属天子封的属国,地位尚在我齐国之上。论版图辽阔,纪国东至安丘,南到临朐东南,西距我临淄不过百里之远,不但不输我国,还是我临淄安定的潜在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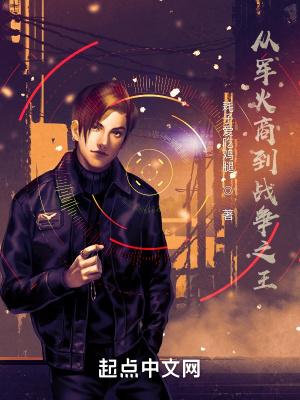
![[原神]杀死那个雷神](/img/16528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