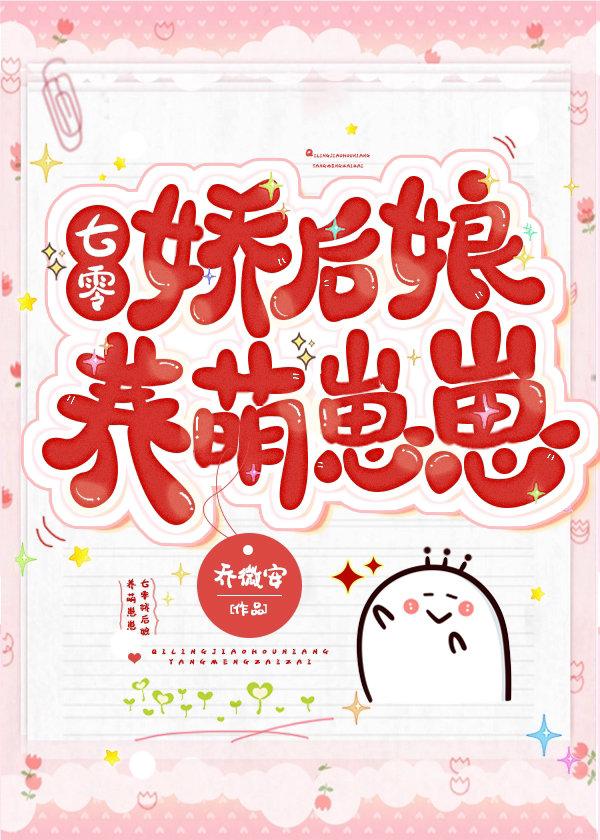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长公主升职手札 > 第346章(第2页)
第346章(第2页)
祠部尚书袁放之裹挟着满身水雾进殿,跪坐禀报时,水珠顺着进贤冠往下淌个不停。
“殿下明鉴,嘉平公主婚事早定,如今只余下请期亲迎。太史曹拟定的良辰吉日,在三日之后。”
“把陪送的合欢席换掉,嘉平公主不喜欢鸳鸯。”成之染翻看案头的聘书和礼书,又细细叮嘱了一番。
袁放之将她的吩咐一一记下,忽而听上首问道:“当年袁妃出嫁时,可是尚书送她离家的?”
袁放之登时一僵,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太平公主面容平静,仿佛只是寻常问话而已。他垂首称是。
成之染微微颔首,半晌道:“到时候让太子送嘉平出宫。”
袁放之领命。
嘉平公主出降那一日,到延昌殿与成肃拜别。云屏后传来断续咳嗽声,成肃被成之染搀到外间,颤颤巍巍地坐在大殿上。
嘉平公主的抽噎声戛然而止。她望着高堂之上暮色沉沉的帝王,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见到次女凤冠霞帔的模样,有那么一瞬,成肃突然想起了她的生母,那个十几年来被他刻意遗忘的罪妾朱氏。眼前的少女青春鲜活,依稀仍带着乱军之中那个吴女的影子。他的心已经干涸得如同一滩枯水,再也盛不下许多难以言喻的滋味。
于是他摆了摆手,道:“三娘,好生待舅姑,将来便是一家人了。”
嘉平公主止不住泪如雨下。
十二驾犊车缠满了红帛,碾过御街积水辚辚远去。外间的喧嚣仿佛与宫内无干,成之染扶住父亲摇摇欲坠的身形,掌心触到突起的肩骨。
成肃笑着指向殿外:“我这些儿女,也只能送到此处了。”
————
许是因为嘉平公主大婚的缘故,成肃的身子似乎比往日多了些气力。他有时能从阴冷的御榻起身,在内侍搀扶下慢慢在殿中走动,一步一步数着地上的金砖。
初夏的流莺时不时在檐上婉转啼鸣,隔着层层叠叠的雕梁画栋,成肃寻不到那鸟儿的踪迹,只是抚摸着有些沁凉的鎏金凭几,听成雍陪他闲话旧事。
嘉平公主归宁那一日,他见到了孟元策的次子,那郎君二十出头,许是第一次面圣的缘故,看上去有些腼腆。不过看成颂宜的模样,二人之间倒算得融洽。
成肃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延昌殿中的海棠花开得正盛,一团又一团鲜妍夺目,像是冷清的寝殿中燃起的炬火。他倏忽想起许多年前的这个时候,筹谋北伐宇文氏之时,听从成之染建议,将孟元策从江州调回金陵,是如何棋行险着的一步。
好在如今看来,当初的选择似乎没有错。
内侍静候在珠帘之侧,内殿御案前,成肃正斜倚凭几,听侍中谢夷吾朗读近日的书奏。
摞成小山的案牍,都是成之染代他批阅过的。他大多数时候一言不发,偶尔听到难解处,才出口询问两句。
案旁的金鹤香薰腾起袅袅青烟,谢夷吾的嗓音一如既往地平静。待皇帝挥了挥手,他放下了书奏。
成肃似乎叹了一口气,道:“太平处事稳妥,我不该……多操这些心。”
内侍识趣地为二人添茶,朝帘间一瞥,通传隔着垂帘道:“启奏陛下,太子右卫率丘豫求见。”
成肃抿了一口茶,道:“宣。”
丘豫快步从玉阶踏过,分明是年近花甲的老将军,走起路来仍旧像年轻时一样风风火火。
成肃抬头看着他,眸中竟生出一丝艳羡,见丘豫要行大礼,于是摆手道:“免了,免了。”
丘豫拱手答谢,又问道:“陛下近日可好些?”
他是出身宣武军的元从大将,年轻时随车骑将军谢峤北拒贺楼铁骑,又与寒微之时的成肃一同清剿海寇,后来更是同起于京门,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去岁成肃将他从豫州调回,到东宫辅弼太子,也是存了几分颐养天年的情分。
两人殷殷闲话,谈起了许多旧事,唏嘘感慨之间,成肃禁不住叹道:“董荣若是活着,来年……合办一场甲子宴,多好。”
“董侯可惜,”丘豫道,“陛下若不弃,来年我与杜侯为陛下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