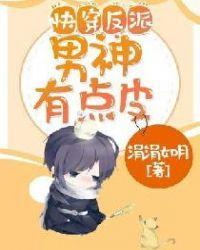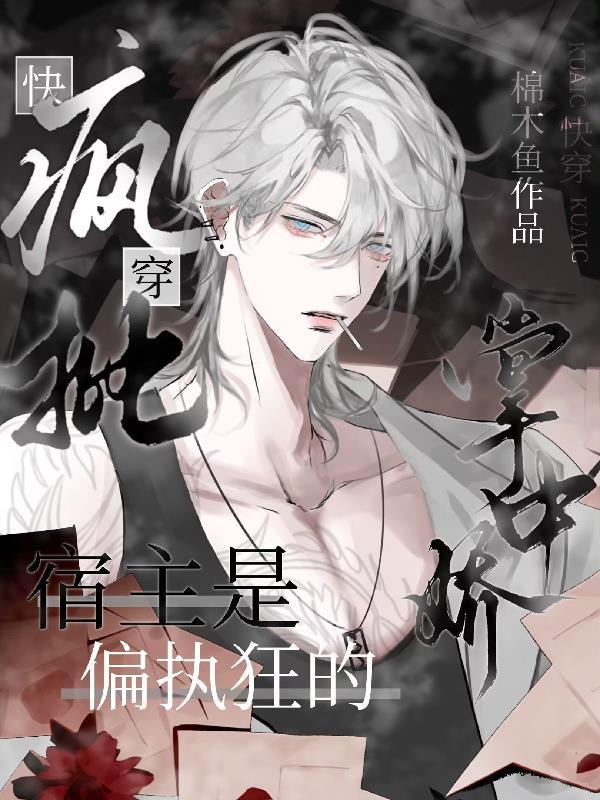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被强取豪夺多年后 > 8090(第8页)
8090(第8页)
十几年来日日如此,除了来她房中勤些,还真看不出来他特别钟爱什么。身居高位,他从不缺好东西。就连最普通的笔墨纸砚,顾太傅的书房里用的是上好的徽墨,墨色如漆,落纸不晕不滞;用纸是宣州的陈年老纸,质地绵密如蚕茧。笔杆是海南黄花梨所制,笔尖是精选的狼毫,就连镇纸,都是一块整块和田暖玉雕琢而成,色泽莹润如脂,精美别致。
可这些宝贝在他眼里,仿佛也只算得“合用”二字,明薇小时候贪玩,把他当时最爱的镇纸砸了一个角,美玉微瑕,她看了都可惜,顾衍也只是淡道:“物件儿而已,不足挂齿。”
她想,顾衍生在簪缨世族之家,不看重这些身外之物。他早年曾热衷于收集名刀宝剑,后来年岁渐长,下面人送些好茶古玩,他看着好就把玩一阵,之后便束之高阁。他的占有欲很强,早年收集那些名刀,即使后来不那么中意,他放在私库里吃灰,也不许别人碰。
……
颜雪蕊想了半天,慢吞吞道:“本宫封你个王爷做。”
十几年如一日,他喜欢权力。
顾衍不屑嗤笑,“微臣德不配位,不敢当。”
他是喜欢权力,可他不看重名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当初皇帝把他打发到翰林院修书,顾衍心平气和,权当养气养神。当个小翰林,或者太傅,抑或王爷,对他而言不重要。他的命令下达四方,莫敢不从,这就够了。
他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要,分明在刁难她!
颜雪蕊气呼呼地松开他的脖颈,挣扎着从他怀里下来,顾衍手臂用力,声音带着笑意。
“好了,好了。看在之前你帮我换药,还算勤勉的份上,我给你一些时间。”
“在此之前,你若为我侍奉笔墨,我允许你旁观。学多学少,看你的悟性。”
顾衍太狡猾了,和他说话一不留神就掉到坑里,颜雪蕊满脸狐疑,“当真?”
顾衍扬了扬下颌,“不如现在开始。”
桌案上的奏折堆积如小山,反正这些东西最后都堆在他手里,不如现在红袖添香,至于颜雪蕊说的“教她”,他只当闺房情趣,一笑置之。
顾衍说话经常春秋笔法,但他守信诺,不说谎。颜雪蕊撑着酸软的双腿从他怀中下来,挽起衣袖,像个勤勤恳恳的小书童一般,拿起磨条研墨。
她的手腕雪白纤细,腕间的白玉镯随着她的动作轻晃,清幽的香气从她的发丝间逸散出来,很快,砚台里漾开了一汪乌亮的墨汁。
顾衍提笔润狼毫,心爱的人伴在身侧,天下尽在他彀中,这世间美事,莫不如此。
颜雪蕊时而凑上前,主动询问。
她的指尖指着折页边缘,蹙起黛眉,问:“这个小镇距京城有千里远,不过下了场雪,值得专门写个折子来?地方官员未免太过清闲。”
顾衍搁下笔,指尖轻叩那行“初三,大雪至,绵延数里”,抬头问她:“蕊儿觉得的,地方官员是闲,还是不敢不奏?”
颜雪蕊一怔,“有区别?”
“当然。”
顾衍的指尖划过落款处,徐徐道:“此处长江以北,冬日下雪是寻常气候,没有什么稀奇。这其中‘绵延数里’,到底是几里,具体是多大的雪,雪后如何?”
“这场雪是否伤了田里的新苗?当地百姓是否受冻?屯粮可够?粮价是否如常?有无商人囤积居奇,趁机哄抬粮价,祸患百姓?”
“再深一些,如若伤了新苗,来年的收成受损,该不该提前调粮,从何处调,调多少?怎么还?”
顾衍一连串问题砸下来,把颜雪蕊砸的头晕眼花,过了半晌儿才反应过来,她咂舌道:“原来还有这等弯弯绕绕。”
她在心里庆幸,幸好让顾衍过目,否则她两眼一抹黑,稀里糊涂,真会耽误了大事。
见顾衍游刃有余地批复,颜雪蕊疑惑又愤怒,“短短一行字,什么都没说,全靠猜吗?这般欺瞒愚弄圣上,何不换一个清廉为民的好官?”
顾衍失笑,道:“人家如实报了大雪,怎么欺瞒你了。”
那些端倪看不出来,只能说明上位者愚蠢。多来几次,底下人摸清了底细,便会欺上瞒下成风,这是王朝覆灭之端。
皇帝坐守京城,然而江山万里,有道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只能凭借一封小小的折子治理天下,怎么批折子,怎么任命官员,从中可见其治世之深浅。
颜雪蕊低叹了口气,语气忧心肿肿,“难道每封奏折都要这样揣摩?”
稍有不慎,便是一个镇、一个县,甚至一个州郡城池百姓的生计,关乎重大,颜雪蕊自觉担不起。
顾衍摇摇头,没有和她解释更多,只道:“日后会好些。”
新帝登基匆忙,地方州郡估计还懵着,这些折子也有隐隐的试探之意,倘若老皇帝在位,即使病重,下面人也不敢这么报。
劳心者治人,下位者并非忠心耿耿,也不是空有一层身份,就有人死心塌地为你做事,正如太子身份显赫,却被顾衍架空,史书上皇帝被宦官、外戚架空,屡见不鲜,徐后让太子多读史书,可惜太子没读进去。
顾衍忽然问:“徐后可还安分?”
他的精力都放在前朝,后宫太后、太妃们,在他眼里,都是将死之人,不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