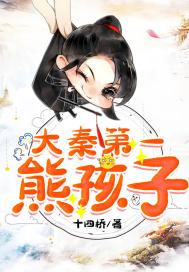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给李隆基直播安史之乱 > 3040(第25页)
3040(第25页)
nbsp;nbsp;nbsp;nbsp;天幕消失,百官身体和精神都放松下来,一夜未睡的疲倦席卷上来。
nbsp;nbsp;nbsp;nbsp;李隆基下令散朝后,众人三三两两结伴出宫。
nbsp;nbsp;nbsp;nbsp;百官手上的记满笔记的白纸轻飘飘的,但他们总觉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nbsp;nbsp;nbsp;nbsp;开元四年十月,姚崇正式递交辞呈。
nbsp;nbsp;nbsp;nbsp;李隆基坐在皇位上久久看着这封辞呈,往事还有天幕的画面一幕接着一幕在眼前迅疾闪过。
nbsp;nbsp;nbsp;nbsp;他最终提笔,批准了姚崇的请辞。
nbsp;nbsp;nbsp;nbsp;虽批准了姚崇辞官,但却没有批准他回乡。
nbsp;nbsp;nbsp;nbsp;姚崇不再是执中书令的首席宰相,但是他是一品开府仪同三司。
nbsp;nbsp;nbsp;nbsp;开府仪同三司,级别最高的文散官,虽是一个虚职,但李隆基专门规定,姚崇每五日来宫中觐见,就朝堂政局以及当时的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是姚崇所说,李隆基一一虚心倾听,并择优采用。
nbsp;nbsp;nbsp;nbsp;李隆基近些时候沉默了很多。
nbsp;nbsp;nbsp;nbsp;人也稳重了不少。
nbsp;nbsp;nbsp;nbsp;闲暇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姚崇递交辞呈的眼神,里面有不舍,还有悔过。
nbsp;nbsp;nbsp;nbsp;姚崇言辞恳切地同他说:“我这一生即将走到尽头,已然如此。天幕与我而言,来的太晚。但陛下,您尚且有挽回之机啊。”
nbsp;nbsp;nbsp;nbsp;姚崇的一句挽回让李隆基又想起了第一个天幕。
nbsp;nbsp;nbsp;nbsp;年份说远不远,但着实不算近了。
nbsp;nbsp;nbsp;nbsp;天幕的内容他已然有些记不太清晰,只记得一个大概。
nbsp;nbsp;nbsp;nbsp;但是李隆基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但事后他总会想起姚崇的眼睛。
nbsp;nbsp;nbsp;nbsp;李隆基最终召来记录当时天幕的史官,把第一次天幕所说的内容完完整整又看了一遍。
nbsp;nbsp;nbsp;nbsp;张说在知道姚崇辞官之后,原本是讷讷不知该说些什么的。
nbsp;nbsp;nbsp;nbsp;没想到姚崇是不当宰相了,但是摇身一变成了开府仪同三司。
nbsp;nbsp;nbsp;nbsp;不仅如此,还要每五日都要来朝上发表自己的政见。
nbsp;nbsp;nbsp;nbsp;心里那点莫名的情绪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顿时烟消云散,暴躁张说又恢复了他本来的样子。
nbsp;nbsp;nbsp;nbsp;不就是辞官吗,有什么好伤感的,他张说未来何去何从命运如何尚且还不知道呢。
nbsp;nbsp;nbsp;nbsp;不伤感了。
nbsp;nbsp;nbsp;nbsp;张说动了动嘴皮子,感觉依旧是如往常一般利索之后放心了。
nbsp;nbsp;nbsp;nbsp;不会说不过姚崇了。
nbsp;nbsp;nbsp;nbsp;不过姚崇现在已然是一个闲散文官儿了,大约也不会跟他起什么冲突。
nbsp;nbsp;nbsp;nbsp;这么想着,张说感觉心都敞亮了些,平日里不是怎么愿意去的早朝,此时都变得值得期待了起来。
nbsp;nbsp;nbsp;nbsp;此时的汴州,倪若水在一堆公文之中忙的焦头烂额。
nbsp;nbsp;nbsp;nbsp;工作,工作,他的心里只有工作,好好工作才能取得政绩,有了政绩才能被调去长安。
nbsp;nbsp;nbsp;nbsp;他爱工作,他的心里只有工作。
nbsp;nbsp;nbsp;nbsp;但倪若水不单单只是在工作,他还在等人。
nbsp;nbsp;nbsp;nbsp;认真工作只是表象,憋着一肚子的气工作才是旁人都看不到的本质。
nbsp;nbsp;nbsp;nbsp;倪若水愤愤把手里看完的卷宗合起来拍到案上,接着又愤愤拿起了另一个卷宗。
nbsp;nbsp;nbsp;nbsp;那两个说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败落刺史,已然被调离长安,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的那两个宦官为什么还不来?!
nbsp;nbsp;nbsp;nbsp;长安到汴州快马加鞭不过才需要五六日的功夫,这都整整十日了,他们就是游山玩水此时才该到了!
nbsp;nbsp;nbsp;nbsp;倪若水心中十分不爽。
nbsp;nbsp;nbsp;nbsp;与他一起不爽的还有两个被下了死命令快马加鞭一定要提前到汴州的张公公。
nbsp;nbsp;nbsp;nbsp;那两个混账!
nbsp;nbsp;nbsp;nbsp;他骑马骑的屁股都快成了八块,他们倒好,真把这差事当玩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