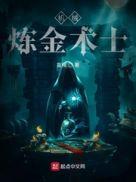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榻下玉GB > 100110(第32页)
100110(第32页)
“我想要,”徐嫣蓦地出声打断,“它不是太傅的孩子。”
这回换茶桌对面的两人愣住了。
不久徐嫣告退,身影走远后,虞白还是没忍住,轻轻“哇”了一声。
燕昭也有同样感叹:“是吧……”
虞白拎起茶壶给她续茶,视线却还望着走远了的人:“会是谁啊……”
“对啊,”燕昭也朝那个方向望着,“她又不出门……”
厅中静了片刻,接着响起“哎哎”的惊呼。
“茶倒我身上了!”
另一边,徐嫣刚到府中,便被叫去正厅问话。
被问及所见,她神态如常,答殿下面色灰败,确有病重不治之相。
张为闻言稍安,命她隔过几日再送拜帖,时常看望,以掌握长公主情况。
被接了拜帖的不止她一个,很快,长公主重病一事便从传言坐成实情。
朝中开始有人奏请收回其摄政之权,请陛下亲政,然而第一个提出反对的,竟是幼帝本人。
一封封信函送进望春园,有的从内廷来,写满担心依赖之语,有的详细记录朝臣情况,谁仍然坚定,谁终于倒戈,事无巨细呈在燕昭眼前。
其中最令她惊喜的,是停职近半年的裴永安终于松口,上奏致仕,举荐次子继任,统领左羽林军。
这比她预想的还要早,许是裴永安当真相信她时日无多,也许与她“病重”以来,裴卓明一直勤恳扮演孝子有关。
只是这样一来就不便见面相商,只能密信往来。
燕昭在望春园的小花厅里忙着,虞白也没闲着。他几乎每日都往外院花园里跑几趟,看那棵高大的桐树。
春风一点一点暖了,花园里景致一日一变,两人几乎看遍了所有春花。
唯独这棵桐树不应春,光秃秃的树枝空指天空。
虞白心里十分焦灼,想要半夜给它打灯笼,被燕昭以树冠太高为由一口回绝。
他又想回府看看去年移栽的那棵开花了没,又被燕昭以城内人多眼杂为由再次否决。
他也想安心地等,但看着传送密信的人来得越发频繁,前来拜见看望的又都被拒在门外,他心中隐约有了某种预感。
快到时候了,他想。
他不怕和她一起冒险,他也不愿去想那个危险的万一,但他总觉得不该带着遗憾。
又一日深夜,睡前,虞白提着灯绕进花园,仰头看空空的树枝。
身后突然覆上体温,燕昭脚步无声跟了过来,笑说抓到了偷花小贼。
空枝一如往常,他失落地要走,又被人拽着留下。
燕昭握着他的手举高提灯,微弱灯影照亮之处,枝头颤巍巍悬着一簇花苞。花苞饱满,像一个个浅紫的铃铛,说不定下一阵春风就会吹开。
一拍即合,燕昭叫人送来茶水点心披风靠垫,拉着虞白坐进那间去岁踏青宴时待过的小亭。
春风入夜也凉,两人挤在一处坐着,看星月下的春景,吃各式各样茶点,并头聊天,天南海北地聊。
虞白到底还是更嗜睡的那个,茶点添过第三轮,他终于扛不住困意,枕在人肩上睡着了。
燕昭独自啜着甜茶,脑中回忆着白日里的安排,反复确认、再三推演,最后统统暂抛脑后,垂下视线,安静数他睫毛。
夜深不知几许,风里绽开甜香。
她赶忙戳戳身旁熟睡的人,“小鱼,小鱼,醒醒。”
“桐花开了。”-
亦是这一夜,一封密信辗转几回,送进张府后院,徐嫣手中。
她展开看过,朝屏风外问:“今儿是几日了?”
“回夫人的话,三月三十。”
片刻,侍女又问:“明日夫人还要去么?已经吃了好几次闭门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