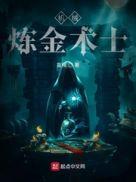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榻下玉GB > 100110(第30页)
100110(第30页)
但这样的坦然没多久就支撑不住了,虞白瑟缩着想蜷起身,双膝也因忍耐而绞起,声音潮湿又破碎,
“轻、轻一点拽……”
没有用。
燕昭按着他小腹把他定在原处,手掌再一滑,他就彻底无力挣扎了。呜咽声高高低低,她索性拎来散落一旁的衣袖给他咬着,还含糊地问了句,那些器具还在吗。
“下次想要个带铃铛的。”-
看得出她很喜欢这个礼物,虞白躺在枕上想。
以往这种时候他习惯趴着,但这次不行了。
躺了一会,还没等到人回来,他挪了挪身子想朝外间张望,可刚一动就蹙眉“嘶”出了声。
挨过那阵刺痛和窘迫后,他想了想,抬手把上半身的被子支起一个小帐篷。
这才好些,他探头朝外:“殿下……已经很晚了,还不歇息吗?”
隔着几重屏风,遥遥传来一句“马上”。
灯台火舌跳跃,燕昭捧着一沓信函,逐一递去焚烧。
第一张是邓勿怜传来,说凉州军已成,随时可动。
第二张是谢若芙传来,说人已送往关内,及时接应。
再往下是些京中变动,她一一看过暗记心中,再后面便是些拜帖,自她“重病”后就没断过,有些送了不止一次。
她垂眸望着其中一张,想法逐渐成型。
提笔,三封信函自望春园发出,一封往凉州,一封往长陵。
第三封,她直接交到下人手里,接着挥了挥身上的纸灰气息,转身朝内室去。
床上的人似乎很是不安,在被子里扭来扭去,见她终于回来后,脸上露出那种可怜又委屈的表情。
燕昭轻“呀”了声,坏心又起,故作担忧问:“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传医官来看看?”
虞白又羞又恼,想探身咬她,但刚动了一下又磨得痛了,瑟缩着跌了回去。
见他眼尾都泛潮了,燕昭这才找回了点良心,摊开手递去个药钵,“涂一点吧,不然晚上都睡不好了。还是我给你涂?”
“……不要。”虞白又把被子撑起一点来,翻了个身侧躺。
方才她去外间做事见不到人,他觉得刺痛难忍,现在见到了,又觉得烫热着心中满足。
他幅度小心地朝人挪了挪,“快睡吧……想抱着睡。”
“不行,要涂的,都破皮了。”燕昭直接上手揭他被子,“明天有客人来,叫人看出异样可不好。”
冰凉落下来,虞白又一缩,忽然发现这样也挺满足的。
但强定心神问:“谁要来?”
“徐嫣。”
“臣妇叨扰,殿下恕罪。”
临湖小花厅,茶桌对面的女子低身拜礼。
她消瘦得快撑不起身上的盛装了,但面上的端庄仍然滴水不漏:
“听闻殿下抱恙,臣妇心中难安,斗胆前来探望。不想一别才过一年,殿下便憔悴这样许多,真是叫人心中酸楚,还望殿下好生安养,早日康复。”
燕昭抬眸看了看她,又借杯中茶水倒影看了看自己。
已经有意做病弱打扮了,但徐嫣还是更为苍白的那个,也不知哪来的底气说担忧她。
比起活人,徐嫣更像个精密的木偶,只会依照剧本表演,说的也只有设定好的台词。
燕昭不按她的剧本走。她茶盏一搁,幽幽叹气:
“上回相聚,还是太傅办的暖寒宴吧?月前下雪,我还想起你酿的椒酒来,想要问你讨些,奈何身患时疾,沾不得酒,只能抱憾了。”
这是点她那回和张为里应外合,给她灌烈酒想要塞人呢。
徐嫣脸上浅笑一滞,面色好似更苍白了:“殿下说笑,臣妇手艺拙劣,哪里值得殿下惦念?殿下未曾怪罪臣妇笨拙无能,臣妇便已感激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