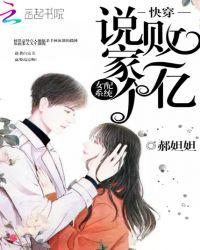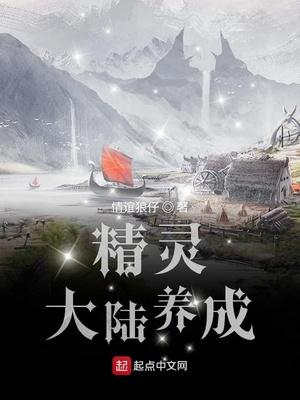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悟南柯 > 知己(第2页)
知己(第2页)
金箔铺洒在竹叶间,碎成点点波光,而在光的来处,云雾被一层层拨开,阳光便趁势穿梭而过,尽情降落在广袤无际的渭河。
“哗啦——”水鸟振翅扶摇,掠过高悬的青天,尾羽拖出一道淡墨。天光浸在水里,水色漫上天边,渭水似被染透,分不清哪是天的青,哪是水的碧,云影也照着云影,整个天地透着一股洗过般的澄明。
微风斜斜吹来,掀起伯喻素白的衣袍,烫金云纹便在光下时隐时现。他右手轻轻一勒缰绳,随风马打了个响鼻,前蹄在软泥上蹭了蹭,稳稳地停住了。
“渭水汤汤,泾渭本分明。如今这日头底下,大夏的沙,柔然的水,搅和在一块儿,倒成了这片金灿灿的好光景。”
伯喻闻声转头,见了来人,眼中掠过一丝复杂,随即恢复平静。他下马站定,微微颔首:“杨伯父。”
杨涛收敛了些许笑容,欠身作揖:“殿下。闻名久矣,无奈多年未得机缘,今日老天赏脸放晴,我这老头子的心愿也成了。”
伯喻微笑道:“您客气了。听您方才所言,似乎也常来此处?”
杨涛看着伯喻年轻的面容,又瞥了眼波光粼粼的河面,露出一抹老兵痞式的笑意:“我是个没名器的,睁眼除了三餐一榻,就是四处闲游。渭河是个好地方,怎能不来?只不过,总有些人非要分个界限分明,哪儿是柔然,哪儿是大夏,平白煞了风景。你说说,他们就跟这水里扑腾的傻鱼一样,白费力气不是?”
伯喻听了他的话,无奈又了然地笑了,他顺着杨涛的目光,也望向河面:“伯父的话,言浅理深。”
杨涛沉默片刻,似在斟酌词句,声音中的轻佻已经敛去:“这水啊,总让我想起故人,想起……明玥公主。”
伯喻身体一震,转首看向杨涛,眼神专注,静待下文。
杨涛从怀中取出一方用油布仔细包裹、蜡封完好的旧笺,珍重地递向伯喻:“当年流言纷扰,说公主奔赴越州,是为寻我私会。”他脸上露出略带嘲讽的苦笑,“这口黑锅,老头子我可是背了半辈子,也连累了公主清誉……唉。”
伯喻的目光紧紧锁在那方旧笺上,呼吸似乎都轻了几分。
杨涛的语气转肃:“那年,公主冒险前往越州,实属无奈之举。其实,她早已察觉章家狼子野心,但放眼朝野,无一人可托付。后来,她得知我尚在人世,且彼时在军中还有些门路,便决定亲赴越州,将一件关乎两国国运的紧要之物托付于我,为的,是求一线转圜。她此行,是为家国大义,绝非私情!可惜,她未能见到我,便……”他声音微哽,顿了顿,强压下情绪,“虽未能如愿亲见,公主却托了极信任之人,辗转将此物交予我手。我想,如今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伯喻伸出手,指尖带着轻颤,接过了那方陈旧的密笺。他凝视着完好的蜡封,微微一滞:“伯父……从未打开过?”
杨涛直视伯喻的眼睛,坦荡而释然:“不曾。殿下,这里头的东西,非同小可。”他目光望向远方,带着沉甸甸的牵挂,“那时,我已有了柯儿和玉瑾。我这条命,早就不是一个人的了。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牵连甚广。我不敢赌,也不能赌。”
沉默在两人之间流淌,只有渭水的涛声和风吹衣袂的轻响。
伯喻双手紧握密笺,油布在阳光下泛着穿越岁月的幽光,他感受着它的分量,也感受着杨涛话语中的无奈与责任。他眼中的最后一丝疑虑彻底消散,转而是更深的理解和痛惜:“原来……多年心结,竟是天意弄人。伯父,累您蒙冤负重,也多谢您,替母亲保全此物。”
杨涛忽然后退一步,对着伯喻,极其郑重、极其端正地行臣子大礼:“臣,江云尧,敬拜殿下!”
礼毕,他并未起身,仍俯身维持着恭敬姿态:“柔然与大夏,战火绵延,多少生灵遭此涂炭。渭水为之呜咽,两岸共此悲戚。殿下胸怀丘壑,此番出使柔然,力促和谈,乃苍生之幸!臣,恳请殿下,务必斡旋周全,为天下平息干戈!若真能盼来太平,明玥公主在九泉之下,也当含笑瞑目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许,真挚而恳切:“这最后一句……是为柯儿,也是为臣自己。”他再次深深一揖,“多谢殿下宽怀大量,未因旧怨迁怒于杨家上下。更多谢殿下于危难之际,舍情取义,保全柯儿性命!此等救命大恩,杨涛铭感五内,没齿难忘!”
伯喻静静地看着深深躬身的杨涛,没有立刻去扶,而是将握着密笺的手紧了紧,目光越过他,再次投向那滋养着两国子民、承载着无数故事的渭河。
河风猎猎,吹动他素白的衣袍,也终于吹散了他眼底沉积多年的阴霾和忧伤。
终于,他目光转向杨涛,伸手将他扶起,眼中郑重而坚定:“伯喻所作所为,皆是心甘情愿。此身此心,既承两国之血,便该负万民之望。伯父所托,母亲之愿,苍生所求,此番前行,断然不会辜负!”
万度霞光,泼洒而下,拥住奔流不息的长河。
少年白衣,立谈中,生死同。海阔天空,前路漫漫,一诺千金重。
![一胎三宝,但男主生[GB]](/img/18940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