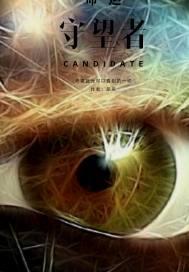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咸鱼她字字珠玑 > 第162章(第2页)
第162章(第2页)
真到了那时,父亲一定会杀了他!
张世景咬紧牙关,他憋屈地在风中扭过头,看见残破站旗下的那身黑甲。
叶帘堂。
兔羊追了上来,将腰带卸作马鞭猛地抽向张世景身下的战马,吼道:「看什么?!还不快走!」
秋风掠过奔途,爽利地带走落叶,将小苍潭的血腥气彻底遗落在身后。兔羊带着稀稀拉拉的兵穿过凛风,足足绕了一个多时辰来确保身后没有追兵,这才绕进山道,往守备营的方向赶去。
「这仗得赢,兔羊。」张世景面色铁青,心火热腾腾灼着,沉声道:「武卫营的弟兄们大都是我带出来的,这仗要是能打倒叶氏,我父亲兴许能放过我……」
兔羊叫人在山道密林处下马,徒步往山上去,以免露出过多的途径痕迹。闻言,他点了点头,说:「明日一早我会带兵回击。」
「如此甚好。」张世景咬着牙,声音都撞进呼啸而的风里,「女人狡诈,这仗算不得数!」
「输了就是输了。」兔羊忍无可忍,「不要找藉口。」
张世景闷哼一声,回首去看身后得以逃生的残兵,他们大都腰佩长刀,灰头土脸,是出身于武卫营
的士兵,这样一比,重甲步兵几乎是在方才的那场战役中全军覆没了。
他恨得牙痒痒。
阆京正规军与叶氏府军的头一次交手,南府军便冲掉了正规军的重甲前锋。除却岭南战役,如今算是张世景头一回正儿八经地带兵做主将,就这样在叶氏跟前翻了车。
思及此处,张世景觉得像是被人陡然甩了一巴掌。满脸通红。
「我要杀了她。」他咽不下这口气,低声喃喃道:「我一定会杀了她。」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走在最前的兔羊忽然停住脚步,回过身,粗糙的手掌猛地扳住张世景的下颚,让他低垂的头正朝着自己,目光也停在他的眼中,「那就冷静下来。」
兔羊手劲大,张世景吃痛地挣扎开来,捂着发红的下巴皱眉,「你简直无法无——」
话音未落,兔羊便一拳头砸在他的肩膀上,砸得他登时失去重心,一屁股跌坐在地,还没等张世景怒骂出声,兔羊的声音便在他头顶响起。
「这里的每个人都想杀了叶帘堂,并且抱有比你这个胆小鬼要大得多的决心。」兔羊沉声说:「失去理智的人会变得毫无用处,而没用的人是不配待在战场上的,你最好明白这一点。」
「你敢推我。」张世景跌坐在山道边的落叶里,不可置信地开口:「天下兵都只属我父亲一人!而你,区区南夷蠢货,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因为你打不赢仗。」兔羊冷冷地垂眸看他,「你只会缩在军阵最末讲一些异想天开的东西,事实是,你甚至连刀都挥不好,懦夫。」
「我——」
「怎么?」兔羊问:「我有哪里说得不对?」
张世景瞧见兔羊赤红的双眼,刚要张开的嘴又老实闭上。他沉默片刻,抬手抹了两把眼睛,从地上爬起来,默默跟在他身后,不再开口。
正规军里气氛低迷,兔羊和张世景再没开过口,连同身后跟随的队伍也不敢随意讲话。他们又徒步走了快半个时辰,有些伤员早已体力不支,被同伴们搀扶着,好在他们终于走到了守备营。
营地接应的士兵们见此,急忙将人往帐里引。张世景跟在最后,却不想进去,便坐在山道里啃馒头。
馒头冷硬,就着寒风吃得感觉实在不好受。张世景越吃眼前越模糊,忽然一双手递来水壶,他连忙蹭掉眼角的水,抬眼瞧见一张眼生的少年面孔,瞧着装束,他该是武卫营死里逃生的一员。
「您喝。」那人又将水壶往前递了递。
张世景没接,恶声道:「滚开!」
那人却没用动,只是俯身将水壶放在他的手边,轻声说:「其实我觉得那南夷说得不对。」
闻言,张世景猛地抬头,「你……」
「胜败乃兵家常事,行兵打仗怎么可能毫无败绩。」他说:「郡公,您是大将军府上的长子,他凭何那样对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