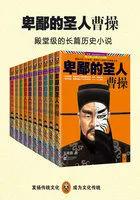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咸鱼她字字珠玑 > 第128章(第2页)
第128章(第2页)
剑刃薄而坚韧,线条流畅,刃纹隐现,似是白虹吞饮山涧水,难掩锋芒。剑柄由古木雕琢,色泽温润,握如美玉。
还没等她细细看过,房内的窗忽然被一把掀开,只见王秦岳一个鹞子翻了进来,目光直直盯着它,嘴里还念着:「宝贝!宝贝啊!」
那头丛伏没拉住人,便伸着手呆在了窗户边上,许元疏移开两步,像是才经过这里,还不忘装模做样地往里瞧了两眼,问:「怎么啦?」
叶帘堂赶忙将剑护在怀里,挡开王秦岳伸来的手,看看那窗,又看看另一边敞开的木门,惊道:「你是土匪吗?!」语罢,她想了想,这人先前还确实是个土匪,便闭上了嘴巴。
「嗯?」王秦岳抹一把额上的汗,笑道:「走窗方便嘛,方才过于激动了……哎!别藏别藏,快让我再看看!」
「只许看,」叶帘堂打开他的手,「不许摸!」
「只看只看。」王秦岳点头,「绝不动手。」
闻言,叶帘堂这才将剑抽了出来,烛火微晃中,刃光亮如雪浪,王秦岳黢黑的面容都被他闪亮了许多。
他呆呆得瞧了半晌,说:「好用!梨木柄轻,与你正是相配!谁给你打的?」
闻言,叶帘堂轻轻挑起嘴角,说:「……旧友。」
丛伏看了看她,没有戳破。
王秦岳点了头,赞了良久,忽而想起什么,歪头问:「起名儿了吗?」
叶帘堂抬起剑柄,摇了摇头。
「起个名字吧?」王秦岳笑着看她。
叶帘堂的眸光在剑身上停了片刻,白虹饮涧,捣珠崩玉。
「就叫『崩玉』吧。」她轻声说。
晚膳时几人用了些粥,王秦岳将朱州地图摊开在案几,叶帘堂正慢慢看着,忽觉自己心跳声愈来愈大,她蹙眉抬眼,见几人不约而同地向窗外看去。
不是心跳,而是战鼓。
丛伏这半价小院离群索居,城门的声响遥遥传来,像是另一个世界。不消叶帘堂吩咐,丛伏便闪身出了屋子,猫儿一般隐匿在黑暗中了。
王秦岳将米粥喂进嘴里,说:「这么快,那位程将军也太心急了一些。」
「他越心急对我们就越有利,」叶帘堂搁下勺,向侍从吩咐:「城门防守薄弱,去告诉瞑君让他的人尽可能坚守,尽量挺过今晚。」
「是。」侍从领了命,便急急上马去了。
闻言,王秦岳撇了撇嘴,叹道:「真是可怜,守城勇士的死亡都是无谓的,不过都是为掌权者铺路。」
叶帘堂垂下眼,「没有办法。」
「是啊,没有办法。」王秦岳喝了茶,将手撑在身子后,透过小窗去看外头漆黑的夜色,「这样想来我们千子坡那时是真的仗义,从不为了自己而叫人去送死……真是生不逢时了,要是那时收敛一些,如今和张氏抢天下的,说不准就是我们了。」
叶帘堂笑笑,说:「杜鹏全过于多疑,而你又过于心软。这是致命的弱点。」
王秦岳望着朦胧的月光从云后透出,顺流而下。他挑了眉问:「是吗?」
叶帘堂抿着茶水,没有说话。
于是王秦岳又点点头说:「是吧。」
千子坡充斥着贪婪,背叛与好战,所以迅速崛起,又迅速陨落。
「都是命数。」王秦岳咂着嘴说。
没一会儿,丛伏便从暗中闪身进屋,左襟沾了一小串泥点,她垂首道:「主子,阆京的正规军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幸好位置较偏,叫近军给冲下去了。」
闻言,王秦岳哼笑两声,语气嘲讽,「他的人海战术起效果了。」
「朱州城被破或许要比我们计划中的快,」叶帘堂皱了眉,低声道:「我们现在就得换衣,准备动身。」
王秦岳的目光转向叶帘堂,笑道:「你倒是没怎么变。」
行动迅速,铁石心肠。
叶帘堂将右手的钢针缚得更紧一些,说:「我只是有决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