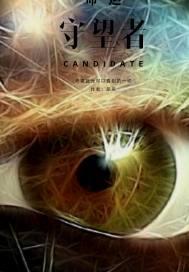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清冷遇疯批 > 8090(第33页)
8090(第33页)
nbsp;nbsp;nbsp;nbsp;她紧张之色,让原浮生不忍,“要不然,你在我书院里教书如何,教教她们如何应对科考,我给你月钱。”
nbsp;nbsp;nbsp;nbsp;“三娘。”颜执安忍不住放下书,她有事可做,不想听三娘唠叨,便道:“你的学生呢,她们又打架了,赶紧去瞧瞧。”
nbsp;nbsp;nbsp;nbsp;原浮生识趣,闭上了嘴巴,躺在躺椅上,摇摇晃晃,不觉间睡了过去。
nbsp;nbsp;nbsp;nbsp;长久无声,颜执安发觉不对,蓦然抬首,却见那人睡了过去,还是春日里,也不盖条毯子。
nbsp;nbsp;nbsp;nbsp;她站起身,在屋内找了一圈,找不到毯子,转而将自己外出的披风取过来,搭在三娘的身上。
nbsp;nbsp;nbsp;nbsp;外间春色正好,距离她假死离开已过去一年多了,小齐还是不能忘吗?
nbsp;nbsp;nbsp;nbsp;事已至此,她已无念想,唯有遥盼皇帝身体康健,早日放下旧事。
nbsp;nbsp;nbsp;nbsp;这一年来,她时刻在意京城的动向,未曾听到皇帝昏聩、荒淫之说。皇帝很乖,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懈怠朝政。
nbsp;nbsp;nbsp;nbsp;先帝在天上,必然会保佑皇帝。
nbsp;nbsp;nbsp;nbsp;颜执安阖眸,享受着春日暖和的阳光,心中哀叹,希望皇帝早日醒悟。
nbsp;nbsp;nbsp;nbsp;皇帝是否醒悟,颜执安不知,季秦却知晓,皇帝就是执迷不悟,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如今无人敢提立皇夫一事,就连李家诸人都夹着尾巴做人。
nbsp;nbsp;nbsp;nbsp;饶是如此,惊蛰这日,皇帝动手,以结党营私之名,捉拿李家几位郡王。其中有位郡王还是齐国公的小舅子,齐国公惶恐之余,搬出前左相仁慈一说,这才让皇帝罢手。
nbsp;nbsp;nbsp;nbsp;可惊蛰这日后,李家人人惶恐,哪里还有心思享受春日的风光。朝臣这时终于醒悟,与李家人保持警惕。
nbsp;nbsp;nbsp;nbsp;先帝在位时,李家这些公主常有不敬,先帝仁慈,不予计较,当今圣上似乎不想维持自己仁君的名头,该清算的则清算,丝毫不会手软。
nbsp;nbsp;nbsp;nbsp;清明这日,城外坟头上又添了几座新坟。
nbsp;nbsp;nbsp;nbsp;皇帝想起远在金陵的左相坟茔,唤来季秦:“清明已过,你怎地不去祭拜老师。”
nbsp;nbsp;nbsp;nbsp;不仅她未去,应殊亭也没去,但她派人去了,她已是左相,脱不开身,便派了心腹去扫墓。
nbsp;nbsp;nbsp;nbsp;季秦大大咧咧,哪里注意到这些细节,被问时,脑海里一片空白。
nbsp;nbsp;nbsp;nbsp;她正准备搪塞过去,皇帝开口:“左相在世时对你不薄,似乎不过二十个月左右,你就将她忘了?”
nbsp;nbsp;nbsp;nbsp;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季秦不敢反对,刚想辩驳,皇帝冷笑,道:“如此不敬,岂可做朕的鸿胪寺卿。”
nbsp;nbsp;nbsp;nbsp;不得了,要被罢黜。季秦忙给自己求情,“陛下,外邦事务繁杂,臣无法脱身,冬至之日必然会亲自过去。”
nbsp;nbsp;nbsp;nbsp;“你有应相忙吗?”皇帝反问。应殊亭成为左相后,她便称呼她为应相,左相一词,似乎还留给了颜执安。
nbsp;nbsp;nbsp;nbsp;季秦欲哭无泪,我是真忙啊,谁没事惦记着死人……而且不在京城,是在金陵啊,相距那么远。
nbsp;nbsp;nbsp;nbsp;皇帝凝望她,将她的表情收入眼底,见她毫无悔过之意,语气冷冽,“拖下去,杖三十,伤愈后,徒步前往金陵。”
nbsp;nbsp;nbsp;nbsp;季秦:“……”你说的是人话吗?
nbsp;nbsp;nbsp;nbsp;“陛下,臣错了,陛下,您听臣解释……”
nbsp;nbsp;nbsp;nbsp;皇帝厌恶,一眼都懒得看,摆摆手,让人拖下去。
nbsp;nbsp;nbsp;nbsp;季秦无辜极了,压在凳上挨了一顿板子,疼得龇牙咧嘴,抬回府上,一想起徒步前往金陵,哭都哭不出来了。
nbsp;nbsp;nbsp;nbsp;晚间,应殊亭悄然而至,怪罪她:“你怎能忘了这件事。”
nbsp;nbsp;nbsp;nbsp;“我好忙啊,老师素来不在意这些细节,她爹死了,她清明也没有去扫墓,陛下是故意的。”季齐心中埋怨,趴在床上,疼得直抽气。
nbsp;nbsp;nbsp;nbsp;“你最近是不是找你媳妇去了?”应殊亭疑惑一句。
nbsp;nbsp;nbsp;nbsp;季秦哑然,软趴趴地俯身,冷哼一声。应殊亭提醒她:“你找媳妇有时间,没时间吩咐人去拜祭老师,不打你打谁?”
nbsp;nbsp;nbsp;nbsp;季秦咬牙切齿,恼恨道:“她最近是不是杀人杀疯了,我觉得我若不是老师的学生,脑袋也没了。”
nbsp;nbsp;nbsp;nbsp;灯火噼啪作响,应殊亭没有回答她的话,而是说道:“陛下如今的性子,阴晴不定,行事霸道,谁敢劝说。季秦,我宁愿老师活着。”
nbsp;nbsp;nbsp;nbsp;她的语气低沉,季秦也沉默,说不过话来,确实,老师落在,陛下岂会这般狠厉。
nbsp;nbsp;nbsp;nbsp;“能怎么办呢?你给我求情,我去金陵也可,徒步就算了。等我走到明年也走不到啊。”季秦惨兮兮地揪着师姐的袖口,“师姐、好师姐……”
nbsp;nbsp;nbsp;nbsp;“我不敢。”应殊亭抽回自己的袖口,面色凝重,“陛下这般,谁敢为你求情,打我罚我也就罢了,万一牵连应家呢。”
nbsp;nbsp;nbsp;nbsp;如今的皇帝并非只罚一人,而是牵连整个家族,那位言官,更是斩三族。
nbsp;nbsp;nbsp;nbsp;“等我回来,也该过年了。”季秦浑身无力,“老师啊,你快给她托梦,告诉她,我是无辜的。”
nbsp;nbsp;nbsp;nbsp;“老师生前找要钱,老师死后要她保佑,你是谁?就算保佑也是保佑她的养女。”应殊亭冷漠地站起身,无奈道:“季秦,不是我不给你求情,而是不敢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