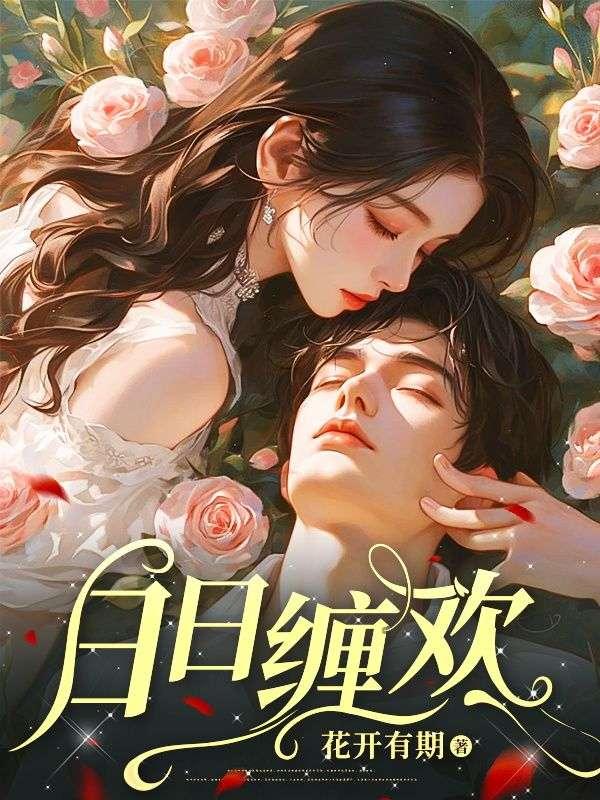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女驸马但误标记太后 > 3040(第9页)
3040(第9页)
“让你淋雨你也不会真去淋雨。”她气鼓鼓地回。
“嗯,是啊,所以就是妻主不忍心看兰时淋雨了。”
呸呸呸,全是自己解读。
“这么大的伞,淋得了什么!”她仍旧气呼呼,声线连自己也未察觉地软了下去。
没气势。
她其实看见了,适才慕兰时为她打伞时,湿过的半边春衫。
话音未落,慕兰时忽然驻足。伞面微倾,漏进几缕天光描摹她眉梢:“娘娘可闻见新焙的龙井香?”
她的指尖,轻点着远处茶坊飘摇的旗帜,“若此刻折返,尚能讨盏雨前茶。”
奇怪,怎么突然就说起茶了?
戚映珠顺着望去,忽觉腕间一紧。慕兰时借着伞面遮挡,将她指尖按在自己潮湿的肩头:“或者……”沾了雨水的睫毛轻颤,“娘子亲自来验,看这春衫浸透几分才算解气?”
雨脚渐密,打湿的柳条扫过伞骨,惊飞两只避雨的黄鹂。
戚映珠别开烧红的脸,却未抽回被握紧的手——掌心纹路里,似乎还留着她方才一笔一划刻下的蜜渍,甜丝丝渗进肌肤。
不管不管不管,就是生气了!
***
暧昧的氛围流连在这柄油纸伞下。
春雨绵绵,路人行色匆匆——她们方才下来的青龙大街,闹了桩大丑闻,王茹恐怕是担心再让百姓聚集在这里,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便找了卫兵遣散众人。
她把直挺挺倒下去的戚中玄带走了。
两人并行走在雨伞下时,偶尔还能听见过路行人的一句“哎你觉得那事是真的吗”,人们仍旧在讨论午后那桩大事。
“谁知道是真是假的呢?不过要我说,要是真的,那京兆尹估摸着也不会认,那北戎细作说是在京中住了七八年,七八年都没有找出来这个细作,这些当官的官帽还想不想要了?”
“也是,算了,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该你我这种人操心,皇帝*操心,世家操心去吧,哎,今年的平绪膏价格似乎又涨了……”
游人的谈笑撞碎在青石板上,慕兰时的指尖仍扣在戚映珠指缝里。掌心相贴处洇出薄汗,像早春枝头将化未化的新雪。
倏然,慕兰时脚步顿了顿,又收拢了指尖,压低声音问戚映珠:“这样就结束了吗?”
她问得轻,却惊起道旁垂柳梢头躲雨的雀儿——那雀儿扑棱棱掠过水面,搅碎满池倒映的碧桃影。
刚刚手掌心的甜意还没有化开。
戚映珠倏然冻住,呼吸凝在沾着雨丝的睫毛间,低头的方寸间,只见雨珠在青苔斑驳的砖缝间绽开。
她知道,慕兰时这是说,她对那些人——对她上辈子如此做的人,报复结束了吗?
她对戚中玄、徐沅、戚姩的报复结束了吗?
“檐角那对画眉尚在交颈,怎忍心教这场雨停得这般早?”慕兰时的音色冷而沉,一点不像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兰芷清香。
戚映珠有一刹那的恍然。
她想起那一天,慕兰时不管不顾地问她:“对,那你敢不敢对我负责?”
豪门世家出身的簪缨贵胄,自会掐断祸患的根脉。何况重来一世呢?
她是权臣。
戚映珠知道,若是慕兰时来处理这事,她定然让这三个人乃至那建康戚氏都吃不了兜着走。
可她不是慕兰时。
“慕相到底是慕相。”她语气成熟起来,笑得有些无奈,眼睫也往下垂着,摇落些许雨丝,缓缓说:“她们已经有了应有的惩罚。戚中玄不必说,他不可能活着回建康了。”
“至于徐沅,她这么一闹,徐氏和戚氏必然互生龃龉,她将来的日子并不太平,但这也算是我和她合作的筹码罢,”戚映珠语气更淡,“至于戚姩,她被那天这两人吵架吓了一大跳,吓出毛病,今后也不知什么情况。”
慕兰时静默地听着,慢慢道:“娘娘真是仁慈。”
戚映珠道:“我不想让她人命运如我一般的浮萍,不可掌握。女子当了浮萍是锁链缠身,做了金丝雀是黄金作笼,我要把她送进宫中去,和那宫中磋磨人的老货有什么不同?”
报复可以,但不要以这种手段报复回去。慕兰时说她仁慈,或许也是——
就像前世,她养花,花败了,而她却总也忍不住把开败的芍药收回妆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