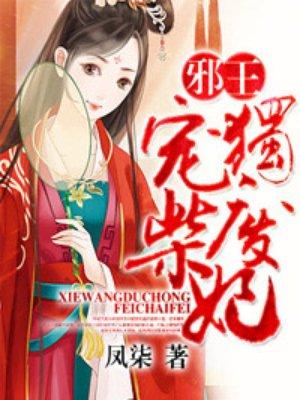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女驸马但误标记太后 > 3040(第4页)
3040(第4页)
“父亲,您醉酒后亲手打的,还记得吗?”她的声音依旧冰冷,像是寒冬里的霜刃,直刺人心。
戚中玄闻言,整个人仿佛被一盆冷水浇透。他张了张嘴,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双手不自觉地颤抖着,脑中一片空白,只剩下那些不堪的记忆不断闪现。
是以,围观群众全部当了真——
围观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骚动。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扼腕叹息,更多的人则是愤怒地低声咒骂。“养外室”、“虐待女儿”的骂声此起彼伏,像是一波波浪潮般涌向戚中玄。
直到一声石破天惊的“父亲,您要是不害自己的女儿,怎么甘心将我们姊妹俩一齐送给一个老鳏夫”出现,众人纷纷又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句话在人群中炸开了花。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原本就已经愤怒的人群更是群情激愤。“畜生!”“禽兽不如!”“这种人不配做人!”骂声如潮水般涌来,几乎要把戚中玄淹没其中。
戚中玄彻底崩溃了。
他跪倒在地,双手抱头,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不!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害她们!我没有!”
然而,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辩解。所有人都认定他是一个虚伪至极的老匹夫,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亲生女儿。
“戚映珠,你说什么呢,难道我要把你嫁给一个老……”他脑内似是炸开了浆糊,只认准一个人说。
这是在说什么胡话!嫁给陛下难道是老鳏夫吗?
大抵真是急火攻心,戚中玄居然把心中所想说了个大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难道陛下就是一个老鳏夫了吗?”
此话一出,本就沸腾的人群更加哗然,立刻就有人大喊了一声:“放肆,竟敢冒犯天威!”
循声望去,正是一个女人,她面阔方圆,神色庄重,双眸锐利似鹰隼,不怒自威,尽显威严之势。这不是别人,正是京兆尹王茹王大人。
戚中玄被这浑厚的声音吼了个激灵,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大脑里面又是一片空白。
徐沅见状,趁机站出来,哽咽着却朗声道:“戚中玄,我徐沅今日就要同你和离!本来昔日,你对我们母女不忠不仁不义就罢了,可是,你养的那个外室,居然是北戎奸细……那我绝不能再忍了!”
这可是株连九族的重罪!
戚中玄嘴唇颤抖,想了想才说:“单、单凭一个香囊怎么定罪?”
这是他唯一的理智了。他纵然不是什么好的父亲,但是这些也不能定罪啊!最多,只是被人戳脊梁骨罢了。
虽然,对于他这种世家出身的人来说,被戳脊梁骨,其实不啻让他直接去死。
要是能够让他直接去死就好了,他现在身上背着的可是通敌叛国的罪名!
“戚中玄,”陈捕头倏地靠近了躺在病榻上的戚姩,仔细嗅闻过后抬声道,“你那香囊味道,正和你大女儿身边这病气味道相似。”
戚映珠道:“正是如此,爹爹他将这外室给的香囊佩戴着,让我们母女都吸入,但姐姐体质特殊,她病倒了。我和母亲找遍了郎中都找不到病源,也是母亲上次被父亲殴打时,错手扯下了他腰间香囊,这才让我们知道原委……”
哀戚着,徐沅立刻也挽起自己的袖口,露出一条狰狞的疤痕:“对,就是他打我!他为了那个北戎外室打我!”
说着,又“呜呜呜”地哭泣起来。
好吧,尽管她和戚中玄就是互殴,甚至可以说是她把戚中玄打得哇哇叫,但眼下嘛,这么多人看着,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想必能够让她们同情自己。
王茹皱着眉,这场闹剧她也知道,只是碍于这的确没违反什么律法,便打算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
可是眼下的发展却愈发出乎她的意料,北戎细作。
今日来京城不太平,她作为京兆尹当然清楚——她前些日子才和陈捕头等人谈过话。
“此事还有疑点……”她开口,却倏然跑进了一个冒冒失失的小吏,双腿颤抖着道:“王、王大大大人!”
王茹眉心瞬间紧锁,神色一凛,沉声道:“有话就说,莫要结巴!”
那小吏双手捧着一套外裳,““王大人,是皇城卫戍营的羽林郎尉张校尉,刚刚他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个自杀的女人,便觉可疑探究了下,发现这女人竟是北戎的细作!”
“张校尉即刻责令小的赶来,向大人您呈报此事……”小吏结结巴巴,额头上沁出细密汗珠,“张校尉眼下正在四处找寻那女子的两个孩子!”
张校尉为人清正,在此前治安、捉拿细作中多有立功,若是她都这么说了,此事必然八九不离十。王茹心头暗自忖度,又见人声愈发鼎沸,害怕事情越闹越大——这可是皇城辇毂之下,断不能出什么差错!
陈捕头忽然想起徐沅刚刚送来的那枚狼牙,想好了后,贴身附耳,命人取来给王茹看。
王茹一见,心下又有了定夺。
她立刻吩咐驱散人群,将戚中玄拿下。
戚中玄见状,惊恐地瞪大双眼,挣扎着想要辩解。两名衙役迅速上前,一人紧紧按住他的双臂,另一人则手持一块洁白厚实的白布,动作干脆利落地将白布对折,而后狠狠塞进戚中玄的口中,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他的叫嚷。
戚中玄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声,身体拼命扭动,却难以挣脱。
![流放后嫁给失忆将军[重生]](/img/1532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