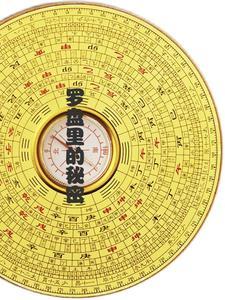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朕那失忆的白月光 > 第120章(第2页)
第120章(第2页)
她得做点什么。
她得时刻提醒他,他不过是个犯错的奴才,不配、也不准再动别的心思。
又是一个下午,暴雨乍来,雷声滚得天地俱白,雨柱砸落,像要将?整座小院吞没。
钟薏坐在坊内熬药,火刚添旺些,在锅底下哔哔剥剥作响。
她侧耳听?着廊下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雨砸在檐角,水声一重一重地盖过来,她却听?得分明。
她冷不丁命令:“去挑水。”
她知道那缸水昨日才刚满,根本?不需要卫昭再去。
只是他干完了?今天的活,前一刻又在门边看她,目光不老实,藏着她最厌恶的那种意味。
她没当场发作,只换了?种方式折磨他,让他滚出去——
去抱着水缸在大雨里走一遭,把那张装得温顺的脸泡烂。
水缸很大,需要双手环抱才能稳住,想撑伞是不可能的。
他若真听?话,就得全身湿透才回得来。
卫昭果然没问?,只应了?一声,抱起水缸,转身出了?门。
钟薏没抬头看他,只在他背影彻底被雨帘吞没那刻,唇角一点点抿直,将?心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意压回去。
院里无井,要挑得绕出坊口,穿过整条主街,再从侧巷回来。
雨砸得极重,一层层水帘封了?天光,
打得屋檐作响。
她低头添了?些柴火,强迫自己不去想。
可不消一刻钟,他就回来了?。
人未入屋,一桶水已稳稳抱在怀中,水线高得几?乎要溢出,却一滴未洒。
卫昭立在门口,浑身湿透。
雨水顺着发丝、眉骨、颧边,一滴一滴滑下来,沿着削瘦的下颌没入衣领。
脖颈苍白,锁骨清晰,连喉结都带着一股冷意。
他没有往前一步。也没出声。
钟薏从药锅前抬头,看到他那副浑身湿漉漉的模样,只觉心烦。
他肯定是故意的——故意站在她眼前,湿答答、死?沉沉地晾着,一句话不说——就等她忍不住。
她偏就不让他得逞。
“你这幅样子想做什么?”钟薏恶声,“走远点,别把我屋子弄脏了?。”
她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可就是忍不住对他刻薄,甚至忍不住想骂他。
卫昭看了?她一眼。
目光不张扬,睫毛垂着,看不清眼底神色,姿态极温顺。
他没回嘴,把水缸放在门口,然后?脚步一撤,重新退回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