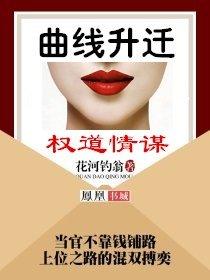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梦魇回响 > 3040(第55页)
3040(第55页)
nbsp;nbsp;nbsp;nbsp;天幕地席,日夜祭奠,庇佑了氏族兴旺,昌盛至今。
nbsp;nbsp;nbsp;nbsp;“太久远的规矩,流传下来已经变了样子。现在贤良镇筹备的祭祀庆典,都是经过李铭书编撰的内容。而他故意隐瞒的那一部分神谕,就明确写了,山里的女人进入祭坛,能够实现愿望,而男人会死。”
nbsp;nbsp;nbsp;nbsp;李司净听完,又一次直面人类的愚昧和外公的苦心。
nbsp;nbsp;nbsp;nbsp;他嗤笑着挑明所谓的神谕。
nbsp;nbsp;nbsp;nbsp;“明明就是男人怕死,才叫女人去死。”
nbsp;nbsp;nbsp;nbsp;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传统,杀死一代又一代的女人。
nbsp;nbsp;nbsp;nbsp;追究起缘由,无非就是相同的原因:
nbsp;nbsp;nbsp;nbsp;因为掌权者是男人,所以女人去死。
nbsp;nbsp;nbsp;nbsp;因为受益的是强者,所以永远给另一方套上弱者的枷锁。
nbsp;nbsp;nbsp;nbsp;蛮荒的弱肉强食,却要被这群家伙盖以“传统”“规矩”“自古如此”,在部分人的私心里,变得冠冕堂皇起来。
nbsp;nbsp;nbsp;nbsp;李司净走出寒潭,风一吹,浑身瑟瑟。
nbsp;nbsp;nbsp;nbsp;他想起半山腰被烧毁砸烂的土地庙,尤为讽刺的说道:
nbsp;nbsp;nbsp;nbsp;“就算这座山有祭坛,五十年前也该被毁掉了。”
nbsp;nbsp;nbsp;nbsp;严城没有出声,走回岸边,撕碎了缠在腰腹的白布,试图裹起流血的伤口。
nbsp;nbsp;nbsp;nbsp;李司净在月光下,见到他手臂凄厉的伤口,流着血,翻开皮肉,像是经历了野兽撕咬,惨不忍睹。
nbsp;nbsp;nbsp;nbsp;看他费劲的,似乎右手已经麻木的失去知觉,只剩左手能够搭把力气。
nbsp;nbsp;nbsp;nbsp;李司净不是烂好人。
nbsp;nbsp;nbsp;nbsp;但他要严城活着,救回他的妈妈。
nbsp;nbsp;nbsp;nbsp;所以直接拿过白布条的另一节,给严城包扎伤口。
nbsp;nbsp;nbsp;nbsp;靠得近了,他才发现白布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迹。
nbsp;nbsp;nbsp;nbsp;读不懂的文字,仿佛是道教的云篆,形成了别样的纹路。
nbsp;nbsp;nbsp;nbsp;这样的纹路染了血,竟让李司净觉得眼熟无比,一时间又无法清楚说出它们的归属。
nbsp;nbsp;nbsp;nbsp;严城没有拒绝,看他帮忙缠好了手臂。
nbsp;nbsp;nbsp;nbsp;“你学过急救?”
nbsp;nbsp;nbsp;nbsp;李司净没有跟他聊天的兴趣,他们仍旧是目的不同的敌人。
nbsp;nbsp;nbsp;nbsp;他沉默的包扎,突然手腕一转,一声不吭的用剩下的一大截布条,将严城手腕也捆了个结实。
nbsp;nbsp;nbsp;nbsp;这才回答:“我还学过怎么制服歹徒。”
nbsp;nbsp;nbsp;nbsp;毕竟他是经历过泥石流、地震、洪水的邪门体质。
nbsp;nbsp;nbsp;nbsp;这种最基本的保命技巧,别人可以随便学学,他必须认真掌握。
nbsp;nbsp;nbsp;nbsp;严城试图挣脱,手腕却像他捆李司净一样紧。
nbsp;nbsp;nbsp;nbsp;他也没多余精力挣扎了,问道:
nbsp;nbsp;nbsp;nbsp;“你要把我丢进祭坛?”
nbsp;nbsp;nbsp;nbsp;李司净不知道他说的祭坛在哪儿,但如实的告诉他:
nbsp;nbsp;nbsp;nbsp;“我会把你丢进派出所,到时候你杀了多少人,都得老实交代,别以为把绑走的两个孩子还回来了,就不用坐牢。”
nbsp;nbsp;nbsp;nbsp;他以为,严城会语气狠厉的辩驳,说自己没杀人或是没绑架。
nbsp;nbsp;nbsp;nbsp;这人却一声不吭,仔细端详他。
nbsp;nbsp;nbsp;nbsp;那样的端详,带着怀念与感伤。
nbsp;nbsp;nbsp;nbsp;严城终于放弃挣扎,垂下捆住的双手,像个认命的囚犯,发出感慨:
nbsp;nbsp;nbsp;nbsp;“你很像她。”
nbsp;nbsp;nbsp;nbsp;“你怎么敢说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