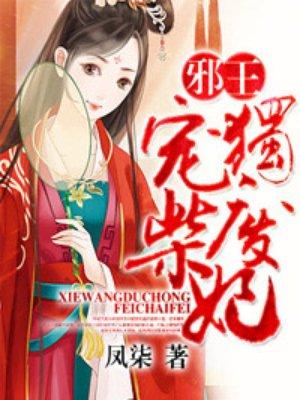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倒霉侦探之哪壶不开提哪壶! > 第384章 她来了(第1页)
第384章 她来了(第1页)
“哐啷”一声,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里,一道刺眼的光照穿透我薄薄的单眼皮,刺向我尚在昏睡的灵魂!
即使我是双眼皮,估计此时此刻也起不到什么屏障作用!
我极度痛苦地挥舞着手,伤口再次裂开,就在我打算鱼死网破的时候,一股清香迎面扑来!
“你就是凌凌发?”
她身着制服,蹲在地上,声音清脆,尽管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却长着一副欧美人的面孔。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没有病,我就没必要问人家的中文怎么这么好,这样愚蠢的问题。
我大口喘着粗气:“不管你是谁,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邀我入伙,至于行动计划、他们的底细、昨晚发生了什么,别说打死我不知道,就是打不死我也不知道……”
“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好,既然你这么个态度,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带走!”
“别动他!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白脸突然化身侠肝义胆的壮士,一声嘶吼划破夜空!
我心头微微一震,看来我平时小看白脸了,就凭这一声怒吼,原来他也是个有血性有尿性的男人!
只见那个女人起身,向前走了两步,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发光发亮的瑞士军刀。
我悬着的心稍微落了落,幸亏不是一把大砍刀,要不然这一刀捅下去,白脸不一命呜呼才怪!
那女人耍着手里的瑞士军刀,冷冷道:“路见不平是不是?见义勇为是不是?拔刀相助是不是?好,我这个人就喜欢成人之美!来人,用这把刀把他的舌头割下来!”
说完,就把刀扔给了旁边的小跟班!
他娘的,这下把我和白脸都吓尿了,这果然是个狠女人!
白脸一头蜷缩进角落里,连哭带叫,大声喊着“不要!不要!”
两个小跟班进到白脸的牢房,也没有多余的话,掏出一把枪,直指他的脑袋。
显然,这是给白脸一个主动选择的机会:要舌头还是要脑袋?
白脸脸色苍白,参杂着累累伤痕,浑身都在哆嗦,他艰难地从黑暗的角落里慢慢往外爬,每一步都是寸步难行!
但两个跟班没那么大耐性,一个扯过白脸的头发,将白脸死死固定在自己的膝盖处,另一个左手将白脸的嘴掰开,右手持刀,准备见机行事。
白脸嗷嗷大叫,又不敢做过多的反抗,绝望的哀嚎在狭窄的牢房里撕心裂肺地回荡!
不行,绝对不行,白脸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我怎么和小英子交待!
凌凌发,你怎么了?编瞎话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吗?
“住手!我说,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那女人阴阳怪气道:“那……你会告诉我什么呢?”
“你想知道的,我都知道……”
“好,很好!早这样的话,何苦让你的狱友经历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带走!”
我冲白脸摆了摆手,接着被那女人的跟班拖了出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许这是我和白脸的最后一面!
……
我被带出了警局,上了一辆私家车,在比勒陀利亚的夜色里左右穿行。
像我这种严重的犯罪嫌疑人,说带走就带走,能有如此权力,可见坐在副驾驶的女人绝对是神通广大的人物。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对方想杀了我,和捏死一只小蚂蚁没什么区别!
![流放后嫁给失忆将军[重生]](/img/1532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