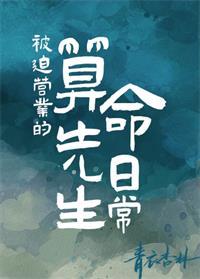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大秦哀歌 > 第458章 国信不可违(第2页)
第458章 国信不可违(第2页)
待赵国新君稳固朝局,国丧大礼完毕,两国邦交事宜妥善衔接,再议归期不迟。”
这“不迟”二字,如同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遥遥无期。
这番话,字字句句冠冕堂皇,滴水不漏地将责任推给了“邦交礼仪”、“新君稳固”、“赵国安全”,彻底堵死了赵佾所有的希望。
嬴政的眼神平静而坚决,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
一直沉默旁观的秦臻,轻轻叹了口气,似是不忍,又似是提醒:“春平侯,还请节哀顺变,保重贵体。
赵国新君即位,已成定局,四海皆知。
质子归国,关乎国信根本,大王非不欲成全春平侯孝义之心,实乃国事维艰,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中苦衷,还请春平侯体谅一二。暂居咸阳,静观其变,方为上策。
相信以赵国新君之明德,必能妥善处理国丧事宜,安抚臣民之心。”
他的话听似劝慰,实则彻底封死了赵佾的期望,并再次强调了“赵国新君”的合法性。
“先生所言甚是。”
闻言,嬴政点了点头,最终盖棺定论,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终结:“正是此理。刘高,春平侯哀毁过甚,心神激荡,好生搀扶,送其回上林苑休息。
着太医令遣良医随行诊视,务必确保无恙。”
“喏!”
刘高立刻躬身领命,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试图搀扶起瘫软在地、面如死灰的赵佾。
此刻的赵佾,额头依旧抵着冰冷的地砖,绝望的泪水无声地滑落。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嬴政的拒绝,冷酷而彻底,将他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幻想与归国的希望,彻底击得粉碎。
“谢…谢秦王…体恤…”
赵佾没有再哀求,也没有再争辩。
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滴血。
他任由刘高和另一名内侍将他从地上架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勉强对着御阶上那个模糊的身影,行了一个僵硬而绝望的叩拜之礼。
随后失魂落魄地转过身,一步一顿,踉跄着、被半搀半架着拖曳向那扇象征着囚禁的、巨大而沉重的殿门之外。
那萧索凄凉的背影,充满了无边无际的绝望与凄凉。
。。。。。。。。。
待殿门完全关闭,只剩下嬴政与秦臻两人时,嬴政脸上那属于君王的、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严悄然褪去几分。
他的目光转向秦臻,问道:“先生,寡人观赵佾此人,已不复昔日赵国太子之姿。依先生之见,此子究竟如何?其心可测否?”
闻言,秦臻的目光也从关闭的殿门收回,眼中并无波澜,他微微躬身,声音平稳如常:
“回大王,臣观赵佾,其心志已如朽木,轰然摧折,徒留形骸。
昔日储君之位,他看似沉稳老练,进退有据,实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错失良机,此非韬晦,乃懦弱无能之本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