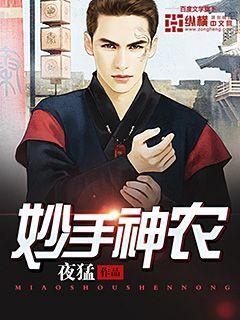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Ben10:和性转小班恋爱冒险 > 番外 僵尸班3(第2页)
番外 僵尸班3(第2页)
忙音在听筒里响起。沫白将话筒还给田马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争取到了时间。
而电话线的另一端,沫妈握着突然安静下来的老式座机话筒,久久没有放下。
客厅里昏黄的灯光映着她脸上难以言喻的表情,那里面似乎揉杂着一丝失落,一丝怅惘,甚至还有一点期待落空后的寂寥。
她对着空茫的听筒,近乎无声地喃喃自语。
“要是会的话,就好了……”
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消散在寂静的空气里。
“像个普通小孩一样”
沫白的父母,真的从未察觉异常吗?那不过是孩子出生时,为人父母者本能地编织给自己的、温柔的谎言罢了。
哪个婴儿会只啼哭一次,便仿佛看透世事般沉寂?
哪个婴孩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阶段,竟能无师自通,快得让人措手不及,仿佛那些技能早已刻在骨子里?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
初时,他们也曾惊喜,将这视为“天赋异禀”的吉兆。
然而,随着时日推移,那份远超同龄人的沉稳,那不合年龄的、近乎洞悉一切的成熟目光,那仿佛跳过了所有懵懂与笨拙的成长轨迹这一切都太过清晰,也太过“离谱”。
沫妈也曾忧心忡忡,夜里辗转反侧:这孩子脑子该不会有问题吧?会不会是某种罕见的“发育异常”?
她偷偷查阅资料,甚至隐晦地咨询过医生。
然而,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冰冷地显示身体健康,精神正常。
没有任何病理上的解释。
最终,沫妈只能选择“摆烂”。
她将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简单又模糊的词汇——“早熟”。
她强迫自己接受这个解释,仿佛这样就能抹平心底那份挥之不去的异样感。
是的,这份“早熟”让她省去了许多寻常母亲的烦恼。
没有夜半啼哭需要安抚,没有追在身后收拾满地狼藉,没有一遍遍教他认识世界却收效甚微的挫败。
她仿佛直接跳过了所有含辛茹苦、鸡飞狗跳的育儿阶段,一步便跨到了孩子“懂事”的彼岸。
然而,省去的麻烦背后,是被悄然剥夺的参与感。
她失去了见证一个生命从混沌走向清晰、从笨拙走向灵巧、从依赖走向独立的完整过程。
那份引导与陪伴的快乐,那种被孩子全身心需要、视母亲为整个世界的满足感似乎还未真正体会,便已消散在风中。
她总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错过了属于一个母亲的、最纯粹的“童年”。
所以,哪怕他们的工作注定漂泊,需要长期出差,哪怕沫白表现得再“懂事”,在沫妈心底最深处,依然藏着一个小小的、固执的愿望。
希望他能像一个真正的普通小孩那样,笨拙地、吵闹地、跌跌撞撞地长大。
会害怕黑暗,会为小事哭闹,会笨拙地表达依赖,会需要妈妈的拥抱和安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仿佛直接跳过了那段理应充满纯真与依赖的时光。
她希望听到他因为害怕而跑回家找妈妈,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那声“哭鼻子找妈妈”的调侃,未尝不是她心底深处一点卑微的期盼。
森林的空地上,篝火终于被田马克娴熟地点燃。
干燥的木柴发出噼啪的爆响,橘红色的火焰升腾跳跃,驱散了四周浓重的黑暗和寒意,在夜色笼罩的森林里,像一颗温暖而倔强的星辰,格外亮眼。
沫白盘腿坐在篝火旁,感受着火焰带来的暖意。
跳跃的火光在他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