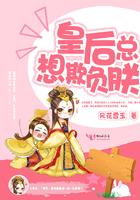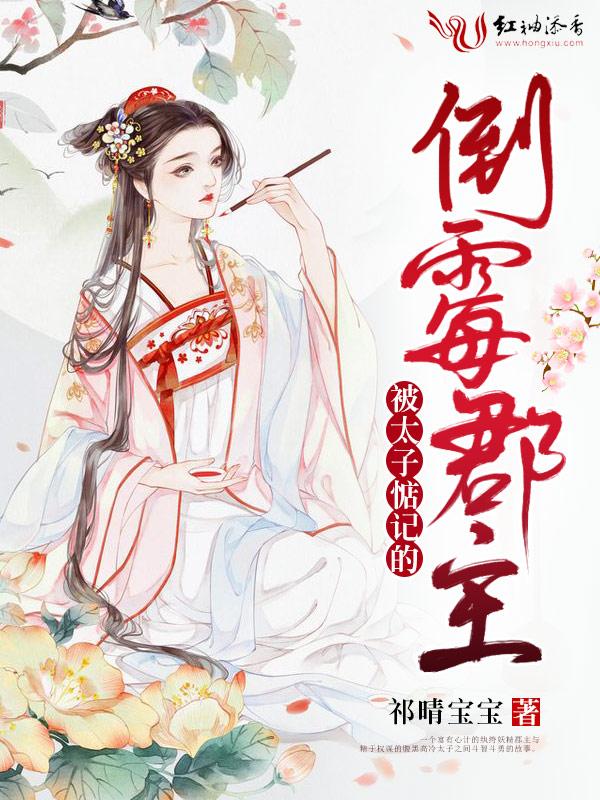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暖暖而生 > 第12章 夏粮(第2页)
第12章 夏粮(第2页)
再看咱陈大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既要统筹整个县衙事务,又要操心越州的夏收,常常是官袍一脱就直奔田头。
风吹日晒之下,那张原本带着书卷气的脸庞也染上了风霜,肤色也黑了一些,下巴甚至冒出了没空打理的胡茬。
官靴沾满泥点,衣袖高高挽起,那样子,哪里还像个县令?分明又变回了当初在五井村和村民们一起开荒拓土、挥汗如雨的那个乡村先生。
两人每天傍晚回林宅相遇时,都会相视一笑,疲惫中透着一种久违的、脚踏实地的满足感——仿佛时光流转,他们又回到了那个一切从头开始的、充满泥土气息的起点。
汗水滴入脚下的土地,也浇灌着他们在越州扎根的希望。
七月的骄阳炙烤着越州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新割稻秆的干燥气息和泥土蒸腾的热浪。夏收的喧嚣刚刚落下帷幕,新一轮的播种便紧锣密鼓地接上茬口。
田间地头,农人们挥汗如雨,翻耕、引水、撒种,一刻不得停歇。
县衙里,陈行宁案头的文书也堆成了小山,忙碌的节奏几乎让人喘不过气,转眼便到了七月中。
紧接着压上心头的,是更为紧要的夏税征收,府库空虚,瘟疫后的重建与储备刻不容缓。陈行宁与林暖私下反复商议,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将那份宝贵的免税恩典留在年底。
夏税,必须收。
“阿暖”陈行宁指着摊开的账册,眉头紧锁,“越州河上游那两个水库,地址已勘定,只待秋末水枯便可动工;迁移安置百姓、开山凿石,桩桩件件都要钱。今年又免了劳役,雇工的钱粮都得从县衙的账目里抠出来。
虽有卖田的收入,到底不及夏粮入库要紧,眼前最大的指望,粮仓必须填满些,否则……”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若再遇灾祸……”
林暖点头,指尖划过账册上标注的预计支出项:“按我们之前分析的,越州冬日,除非像去年那般遭逢大疫,大多还算平和,风雪灾害也少,反倒是夏秋之交,暴雨狂风常至,隐患更大。知远,你自己决定即可!”
她理解陈行宁的压力,这决定意味着县衙要顶着百姓可能的怨言和短期的困难,去换取更长远的安稳。
提到钱,林暖也颇感无奈。
她一手创办的林氏钱庄,如今只在林氏产业内部和关系紧密的工坊间小范围运作,连越州城北都未能完全铺开。
钱庄里确实有些存款,但这点积蓄,仅够支撑林氏自身的资金周转,对于县衙庞大的水利工程开销,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庄最怕的就是坏账,便是……便是上辈子那般精密的信用风控,也难保万无一失,何况如今?
只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一点点试,一点点扩。信誉这东西,建立起来难如登天,崩塌却只在一夕之间。
她还是知道金融的风险,宁可走得慢些、稳些,也不愿为了扩张速度埋下祸根。城北的铺开,还得再等等,再观察。
嗯,夏收完成了,这两年试验出来的酱料也可以投入生产了,城北又要新建一坊。建哪好呢,还是让向义好好琢磨琢磨一个地吧!越州老君观也建好了,竹山脚下的学堂规划也可以提上日程……日子在忙碌与筹算中飞逝,转眼到了七月底。
一封来自祝府的消息,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林暖心中漾开层层涟漪。她的闺中密友,祝萃雅,将于八月底离开越州,返回遥远的北地范阳,完成她的终身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