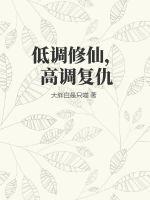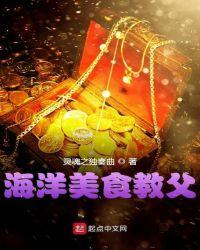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暖暖而生 > 第221章 微光(第3页)
第221章 微光(第3页)
他抱着这轻飘飘的小小身体,仿佛抱着自己正在崩塌的世界。
越州宴,这座雕梁画栋、觥筹交错的繁华酒楼,如今空气中弥漫的气味却令人窒息:浓烈刺鼻的石灰水味,也无法完全掩盖苦涩药汁的辛烈、呕吐物的腐酸以及排泄物那令人作呕的恶臭。
这些气味混合、发酵,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进入此地的人胸口,也全部压在云海道长的肩上。
曾经飘逸出尘的道袍早已不见踪影,他那神奇的改扮之术也维持不住,取而代之的是一件沾满深褐色药渍、不明污迹和点点石灰斑痕的粗布围裙,胡乱系在他瘦削板正的身躯上。
他脸上蒙着的口面边缘被呼出的水汽和汗水浸透,紧紧贴在皮肤上,露出的那双眼睛,曾经清亮有神,如今却深陷在浓重的青黑色眼窝里,布满了蛛网般的红血丝,眼神疲惫、焦虑,深处藏着一种麻木的沉重。
他太忙了,忙得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被被无形的鞭子一刻不停地抽打着。
天刚蒙蒙亮,他就得起床,提着那个装着脉枕和笔墨的药箱,挨个隔间巡视。
里面的病人会把手伸进石灰水里浸泡一下,然后伸出门缝,他得隔着门板缝隙或是在门口保持距离,凝神探脉,细听里面病人虚弱的描述。
每一次触诊,都像是在触摸死神冰冷的指尖。林三爷的脉象沉细无力却一直撑着,三夫人吐到胆汁都出来了还是撑着,卢家有几个年轻后生高热呓语,还有新来的冯家祖孙……脉搏细弱得几乎摸不到的脉息让云海的心狠狠揪紧。
后来冯家祖母也没有留下来,那小娃娃还在苦苦支撑……
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在随身携带、已被翻得卷边的脉案上匆匆记录下“脉浮数”“脉沉迟”等字样,字迹因疲惫而潦草颤抖。每一个判断都重若千钧,他知道自己“实践经验不足”,每一次开方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
本身大夫就不多的越州城已经征召了所有的大夫,东南西北四个区隔离区外都坐镇着一到两名大夫,像他这样的半搭子,也是林宅的希望。
诊脉完毕,便是争分夺秒的煎药时间,原本精致的后厨如今烟雾缭绕,如同战场。几口大灶同时燃烧着,上面架着数个硕大的药罐,一个药罐可以让好几个症状差不多的人喝。
云海亲自守着,大冬天的能让人出一身汗,他不断弯腰查看火候,用长柄勺搅动着罐里翻滚的深褐色药汁。
空气中弥漫着极其浓郁的苦涩气味,熏得人头晕眼花。
药材的数量有限,种类也未必完全对症,他必须精打细算,根据有限的药材和病人不同的症状,调配着剂量和组合。
有时火候稍过,药汁便糊了底,散发出焦苦味;有时水添多了,药效又恐不足。
他手忙脚乱,脸上沾着烟灰,围裙上溅满药汁,哪里还有半分道长的清雅?只有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药罐,那是维系着十几条性命的希望之火。
药终于煎好了,整个药罐连同那极其简陋、几乎谈不上厨艺的餐食——通常是寡淡无味的稀粥,或是煮得发黄发蔫、勉强能入口的蔬菜,有时甚至只有硬邦邦的饼子——一起放在木托盘上。
云海端着沉重的托盘,脚步声伴随着隔间内传来的压抑呻吟、痛苦的咳嗽声、虚弱的呼唤声。
他走到每个隔间门口,将药罐里的药汁和食物分别倒入每个隔间门口的两个粗陶碗里,用沙哑到几乎失声的嗓子喊道:“药好了…趁热喝…”“饭也好了…放在门口了…”有时里面会传来一声微弱的“谢…谢道长…”,有时只有痛苦的喘息作为回应。
他不敢多做停留,放下东西立刻转向下一个隔间,唯有眼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悲悯和力不从心的焦灼。
日复一日,睡眠都成了最奢侈的东西,往往刚刚在桌子上趴一会,就被某个隔间传来的剧烈呕吐声或惊恐的呼叫惊醒。
一开始几天,他感觉自己的体力透支到了极限,端药盘的手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有好几次差点打翻药碗。
精神的压力更是巨大,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挣扎,尤其是看着像杨婶子和冯月这样本就不堪一击的老人孩子迅速被病魔吞噬,那种“保不住”的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
他也会在无人处对着药渣和空了一半的药材筐发呆,眼神空洞,怀疑自己这点微末道行和粗糙的照料,是否真的能“保着一众人的命”?
他甚至会短暂地闪过逃避的念头,但下一声病人的呻吟传来,他又会立刻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走过去。
支撑他的,或许只剩下那点刻在骨子里的道家“贵生”之念,以及林暖等人信任的目光。这十几个在越州宴里的人,他们的命,都悬在的手上,悬在他那被药味浸透的肩膀上。
他像一根不灭的蜡烛,在瘟疫的狂风中,拼尽全力地维持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光亮,照亮这方被死亡阴影笼罩的绝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