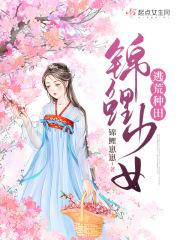千千小说网>大明:寒门辅臣 > 第两千三百八十一章 降落伞飞天之前(第2页)
第两千三百八十一章 降落伞飞天之前(第2页)
写罢,他长叹一声,望向窗外,夜色如墨,风声呼啸,仿佛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就在这时,门外再次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大人,江南急报!”
朱承志接过急报,展开一看,眉头顿时紧锁。
“江南士族已联合地方官吏,强行驱逐书院先生与学子,并张贴告示,宣称书院为‘非法私学’,凡入书院者,皆不得参加科举。”
朱承志冷笑一声:“果然,他们想彻底断绝寒门子弟的出路。”
他沉思片刻,随即下令:“命李慎之与赵子昂,立即组织书院先生与学子,前往邻近府县暂避。同时,命人将此事详细记录,附上证词,快马加急送入京城。”
弟子应声而去,朱承志则提笔疾书,修书一封,命人送往内阁,请求太子朱瞻基尽快下旨,澄清义学书院的合法地位,并严惩江南士族的违法行为。
他知道,士族此举,已不仅仅是针对书院,而是想借此机会,彻底否定义学书院的合法性,从而将书院从国子监体系中剔除。
若让他们得逞,书院将彻底失去朝廷庇护,寒门子弟也将再度陷入绝望。
翌日清晨,朱承志便前往内阁,求见太子朱瞻基。
朱瞻基神色凝重,显然已收到江南急报。
“承志兄,江南士族此举,已属公然挑衅朝廷。”朱瞻基沉声道,“但我父皇病重,朝中士族势力庞大,若贸然下旨严惩,恐怕会引发朝局动荡。”
朱承志拱手道:“殿下,士族已开始行动,若不及时制止,书院将彻底覆灭。寒门子弟的未来,也将被彻底断送。”
朱瞻基沉默片刻,终是点头:“我即刻修书,命吏部尚书尽快拟定授官名单,并下旨严惩江南士族查封书院、殴打先生之罪。”
朱承志拱手道:“多谢殿下。”
他离开太子府后,心中依旧沉重。他知道,士族的反击才刚刚开始,而他,必须在这场风暴中,守护书院,守护寒门子弟的未来。
夜色渐深,京城的街道上,风声呼啸,仿佛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而朱承志,已准备好迎接这场风暴。
朱承志步出太子府,夜风如刀,刺得脸颊生疼。他裹紧大氅,脚步虽缓,心思却如狂潮翻涌。士族此番动作,已非寻常争权夺利,而是有备而来,步步为营。他们不仅要将书院逐出江南,更欲彻底抹去书院在国子监体系中的地位,让寒门子弟再无出头之日。
他心中明白,自己虽已多方奔走,联络翰林院、兵部、大理寺,甚至借太子之力,试图以朝堂之力压制士族,但士族根基深厚,非一纸诏书便可轻易撼动。更何况,如今皇上病重,朝局不稳,王振虽为司礼监掌印,却未必愿意与士族正面冲突。若他借机拖延,甚至暗中纵容,书院的处境将愈发艰难。
“大人,回驿馆吗?”随行弟子低声问道。
朱承志摇头,目光如炬:“不,去户部尚书陈文渊府上。”
弟子一怔,但未多言,立即调转马头,朝户部尚书府疾行而去。
陈文渊年过五旬,为人清廉刚正,虽出身士族,却素来反对门阀垄断,曾在朝堂上多次弹劾江南士族侵吞田地、虚报赋税之事。朱承志虽知其与士族有旧,却也知其心中尚存公义。若能争取其支持,便可在财政上给予士族以打击,使其失去经济支撑,进而削弱其势力。
陈府门前,朱承志下马,递上名帖。不多时,门房出来,神色恭敬:“朱大人,尚书大人已候您多时,请随我来。”
朱承志心中一动,看来陈文渊早已知晓江南之事,甚至可能已在等他上门。
步入书房,陈文渊已身着便服,面色凝重。他起身迎上,拱手道:“承志兄,江南之事,我已知晓。士族此举,实属猖獗。”
朱承志拱手还礼,正色道:“陈大人,书院乃寒门子弟之命脉,若书院覆灭,天下寒士将无以立足。士族若真要借机打压书院,必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清洗之风。若不尽早应对,后果不堪设想。”
陈文渊叹息一声,道:“我虽非士族,却也深知其根深蒂固。若贸然与之为敌,恐怕会遭其反噬。”
朱承志沉声道:“陈大人,士族若掌控天下文教,朝廷将成其私器。您身为户部尚书,若能从赋税、田地、漕粮等处入手,严查江南士族隐匿田产、逃税漏税之事,便可断其财源,令其根基动摇。”
陈文渊沉吟片刻,缓缓点头:“承志兄所言极是。我即刻命人彻查江南士族田产赋税之事,并奏请朝廷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