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大明:寒门辅臣 > 第两千三百七十一章 冯胜羡慕不来的特权(第3页)
第两千三百七十一章 冯胜羡慕不来的特权(第3页)
数日后,京城传来消息,朝廷已正式下旨,允许义学书院学子参加殿试,但需与国子监、府学学子一同选拔,不得越级。此旨一出,朝野震动,士族一方更是哗然。
朱承志收到消息时,正在书房中批阅书院学子的考卷。他放下手中的朱笔,望着窗外飘落的黄叶,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终于,他们也坐不住了。”他低声喃喃。
果然,翌日清晨,书院外便传来喧哗之声。朱承志走出正堂,只见数十名身着儒衫的士子正聚集在书院门前,高声叫嚷,要求废除义学书院,恢复旧制。
“寒门子弟,岂能与我等同台竞争?”一名士子高声喝道,“义学书院不过一群粗鄙之人聚集之所,若让他们入仕,岂非污了朝堂?”
另一人则高举手中书卷,怒斥道:“我等寒窗苦读十余年,方得入仕之望。如今义学学子竟可直通殿试,岂非乱了纲常?”
朱承志立于门前,静静听着,神色平静。他并未下令驱赶,而是任由这些士子发泄。
半晌,他才缓步上前,朗声道:“诸位,义学书院之设,乃为广开才路,让寒门子弟亦有入仕之望。若诸位以为不公,可与书院学子一同赴考,以才学论高下。”
那名高声叫嚷的士子冷笑道:“我们岂会与一群粗鄙之人同台竞技?”
朱承志目光一冷:“若诸位自诩才学,何惧与书院学子一较高下?若诸位不愿同台,那便请回。义学书院,不欢迎不愿公平竞争之人。”
那士子一时语塞,脸色涨红。
朱承志又道:“诸位若真有才学,何不以实力证明?若连公平竞争都不敢面对,又何谈治国安邦?”
人群中顿时议论纷纷,一些士子开始动摇,有人甚至悄然退去。
朱承志趁势道:“义学书院,不求富贵,只求真才。若诸位愿以才学论高低,书院欢迎;若诸位只想空口白话,那就请回。”
那名士子见势不妙,只得愤愤离去,其余人也纷纷散去。
朱承志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却知,这只是开始。
不久之后,各地义学分院纷纷传来士族子弟阻挠书院招生、煽动地方士绅上书朝廷的消息。更有甚者,竟有士族暗中雇佣刺客,意图刺杀书院先生。
朱承志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加强书院戒备,并派遣亲信弟子前往各地义学,协助整顿秩序。
同时,他亲自修书一封,命人送往京城,呈递御前。
他在信中写道:“陛下圣明,义学书院之设,乃为寒门子弟谋出路。然士族不甘失势,屡屡挑衅,甚至不惜动用刺客。若不严加惩治,恐寒门子弟再无翻身之日。臣恳请陛下,明察士族阴谋,严惩不贷。”
信中言语恳切,字字血泪,朱棣阅后,神色凝重。
朱瞻基见状,低声劝道:“父皇,士族若再不加以遏制,恐义学书院难以为继。”
朱棣沉吟良久,终是点头:“朕允你派人彻查士族阴谋,若属实,严惩不贷。”
朱瞻基躬身道:“臣遵旨。”
随即,朝廷下旨,命锦衣卫彻查士族阴谋,凡有勾结刺客、煽动地方士绅者,一律严惩。
此旨一出,士族一方顿时震动,不少人纷纷收敛行迹,不敢再轻举妄动。
而义学书院,则在朱承志的坚持下,继续稳步发展。各地义学分院陆续设立,寒门子弟纷纷涌入书院,求学问道。
朱承志站在书院门前,望着一批批学子步入书院,心中满是欣慰。
他知道,义学之路虽仍艰难,但他已不再孤单。寒门子弟,终将用自己的才学,打破士族垄断,走向仕途。
“莲未凋,灯未灭。”他低声念道。
夜风拂过,吹动他的衣袍,仿佛回应着他的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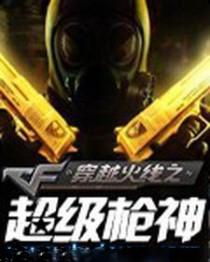
![女配一心学习[快穿]](/img/53993.jpg)
